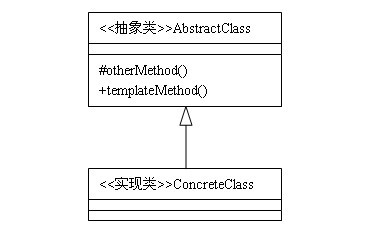在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江明院士学术成长的过程,从中可以体会,在科研工作中如何选题、如何思考、如何创新。文章较长,慢慢看,必有收获。
从相容到络合,到组装
----论文背后的故事
江明教授在高分子科学系博士论坛的演讲
(2004.12.14)
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有机会到高分子科学系博士论坛与大家做一些交流。今天报告的题目是,从相容,到络合,到组装;同时谈谈科研课题的选择和我这些年从事研究工作的切身体会。相容,络合和组装,实际上是三个“关键词”,代表我们过去二十多年研究工作发展的三个阶段。有关的学术内容我想同学们在我的课程中已经学到过了,所以科学内容我不想展开得很深;没听过课,但是有兴趣的同学可以看看我们网页上有关的文章。我主要想谈一谈“论文背后的故事”,也就是说我在研究过程当中是怎样想的,思路如何形成的和我对科研的切身体会。
1. 辛酸往事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要从比较远的事情讲起。我是在1958年提前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只念了三年,就被选出来参加到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的建设中去了。这当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那年我才二十岁,只读了三年书,所以我还只是一个“大专生”。我当时最强烈的想法和愿望就是,科学上太无知了,太想学习了,就是想快学一些东西,多学一些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在文革以前的背景下面,如果你非常想读书想钻研学术的话,你就会被认为是走“白专道路”而打入“另册”,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关于这大环境,下面我还想说得仔细些。
文革前的中国高分子,复旦高分子是什么样子呢?公平地说,当时也做了不少事情,主要是建立和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特别在本科教育方面,培养了不少人,这些人后来为中国高分子的起步和发展建设方面都做了贡献。但是就基础研究这个角度讲,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因为走了一条错误的路线,完全是封闭式的搞科研,同时不断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当时的状况今天的同学可能难以想象,所以我可以举些例子。在整个文革以前,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在国际高分子知名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么?能给出一个回答么?同学都不太知道吧?很幸运,不是零。但是,是多少呢?是“一”,就我所知就一篇文章!(可能在苏联杂志上会有一些,我未调查过)。就是钱人元教授在捷克开的一次国际高分子会议上做的一个报告,是1958年吧。作为这个会议的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Polymer Science上。就我所知,就这么唯一的一篇文章。大家可以想想,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么,复旦的高分子又如何呢?从基础研究这个角度来讲,可以说更可怜了。我们当然没有在国际高分子期刊上发表过文章,从国内讲,当时也有学报的,高分子通讯,化学学报,可我们发表的文章总数,我没有确切的去数过,不过我知道大概是,小于五篇。三十来位教师,近十年光阴,总共发表过小于五篇文章!实际就是这个状况。到了文革以后,这个情况就更糟糕了。当时我被列入化学系的所谓的‘牛鬼蛇神’,最年轻的“牛鬼蛇神”,我和顾翼东,严志弦这些名教授一起从事体力劳动,在化学楼扫厕所,跃进楼后挑河泥。并不断地被批判。当然,被完全剥夺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这种情况一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有比较大的变化。其实,在七十年代初我就算被“解放”了,可是还是被打入另册的。我举个例吧,大约在74~75年的时候,当时中美关系有一点解冻,有一点缓和的时候,美国一个叫Morawetz的教授来访,当时他在科学会堂做报告。其实在这之前我已知道他的名字,因为他写过一本很知名的书,Polymer Solutions,我也学过一些,所以知道这个人。同时我也知道,这是第一个来自美国的高分子学术报告,当然很希望去听听。可是就在他来做报告之前,我就被告知说,“你不能去”。显然,他们是不相信我吧,认为我这样的人很可能跟美国佬联络,里通外国,企图要做偷越国境之类的事情。当时就是把我这个小知识分子想得那么可怕!若干年以后,我在德国见到Morawetz,是在一个很私人的场合,是德国教授请我和他二人吃饭,我想把这个故事当笑话讲给他听。可我最后没有这样做。因为我想,对他来说,这太难理解了,他听了会不会把我们中国人都看作不近人情的怪物啊?再说个例子吧,到了1978年,中美之间已经开始有不少的交流了,当时美国的高分子界派出了一个很权威,以Flory为首的高分子代表团到中国来,要搞一个中美双边的Symposium。你可以想象,当时我们中国哪有办法拿出像样的工作来和人家交流,所以紧张地进行了“选拔”。结果当然也拔不出什么,只能由北化所,应化所的几个老先生和他们稍微进行一些对话吧。然后,Flory到上海来做报告,在我们学校讲过一讲,关于链的构象,我记得很清楚,这时总算让我去听了。若干年以后,我听钱人元教授和我讲过,Flory走的时候,钱先生请他对中国高分子做一些评价,他说:“中国没有高分子的科学研究”。钱先生说,这句话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一个很大的震动。你看,我们忙了那么多年,结果国际高分子界里最大的权威说,你们没有高分子研究,你们所做的一些,是谈不上真正的高分子研究。心平气和地想想,人家讲的是实话,不是歧视。不过,这并不等于说我们从事高分子研究的中国人水平都很差,不是这个情况。我们有很好的一些领头人和代表人物,包括我们的于同隐先生。这样一批老一辈科学家,他们在四十、五十年代就在美国拿了博士学位,冲破很多困难才回到国内来,我很尊敬他们。但那么多年里,他们没有得到正常的搞科研的环境,不断地受到政治运动的干扰,甚至受到直接的打击。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做出好的工作?在这些长辈科学家当中,我比较了解的有钱人元老师。钱先生四十年代就在美国做了很漂亮的工作。现在化学所的韩志超先生,CC Han,就跟我们说起过,他七十年代到Wisconsin大学工作的时候,他们实验室用的一台仪器,可能是介电常数或是光谱方面的,我记不清了,这仪器还是钱人元先生在四十年代在那里造的。他建造的这个仪器一直到七十年代还在很好的工作,所以说他在实验上也是非常的优秀。他的物理的功底是非常的雄厚。我记得,到了八十年代国际交流比较多的时候,有两位国外很权威的学者跟我讲过,像Qian这样能够对于高分子里面这么广泛的问题,如高分子凝聚态的问题,高分子液晶的问题,高分子结晶的问题,高分子溶液的问题,有机导体的问题等等,发表很深刻见解的,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他的科学精神也堪称楷模。去年11月,在他逝世前一个月,我和吴奇老师一同去看他,也是最后一次见他。他说,在动大手术后的病床上,还写了文章,是关于化学动力学中“稳态假设”的。40年代他就为此投过稿,被拒了。他认为自己没错,要再写稿“翻案”….这一席话使我终生难忘了,他是真的把生命和科学溶为一体了。这样的科学家,大家想想,如果他回国后的几十年,有个正常的环境,那么,在今天国际采用的高分子物理教材上,恐怕除了有Flory怎么怎么讲,de Gennes 怎么怎么讲,也应有Qian怎么怎么讲,应该有的。
前面说了,文革前,文革中,我最大的愿望是想学习,想读书,想做研究,可就是做不到。这事情真正发生改变还是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转折,我的命运也发生了转折。正如一首著名的歌里唱的,“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我的春天到来了,我有机会参加了出国选拔的考试。那时,不可能考很多的业务知识,只能考点英文。我在中学是念俄文的,英文基础不好,但是我确实很喜欢英文,所以在文革很困难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英文将来还有没有用得上的一天,但我还是对它“念念不忘”,没有丢掉它。在那个时候公开地念英文,学口语,肯定要遭祸的。我于是买了一本The Quotations of Chairman Mao,《毛主席语录》的英文版,读毛主席的书,没错吧?在这大红伞的掩盖下,我还是学了不少,经过文革,我英文没有丢掉,多少还有了些进步,所以那次考试我考了八十几分,当时有些老师只考了二十几分,因为荒废得太久了。大家不要以为我英文很好了,要知道那份试卷就相当于今天初中生的水平,可笑得很。1979年的春天,我到了英国Liverpool大学,那个时候已经四十岁过了。二十岁我就从大学毕业,可到了四十多岁我才开始我的研究生涯。
2.攀登之旅
到了Liverpool以后我就面临着第一次科研课题的选择。当时因为我们是公派出去的,所以那边的教授还是欢迎我们和他们一道工作,至少是一个劳动力。Liverpool大学有很好的高分子的传统,在历史上是很优秀的。当时有两位老师都希望我跟他做,一个叫Bamford,他是FRS,就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在我去以前我就知道他的大名。因为他有一本书,“The Kinetics of Vinyl Polymerization by Radical Mechanisms”,我在出国以前就读过的。他在自由基聚合方面是权威的,他的文章在不断的发。还有另外一位,名气要比他低的多,就是Eastmond,他也是做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以前是Bamford的学生,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课题组。但他的重点转到multicomponent polymers, 就是多组分聚合物,当时这个是一个新兴的方向。就是把多种聚合物放在一起,看它的物性,看它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我做了一些比较,如果跟Bamford,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但从学科上讲,当时free radical polymerization基本的一些东西已经确立,很难有比较大的发展。从将来回国后的工作来讲,也难有大的贡献,国内已有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工作。而多组分聚合物,虽然很不成熟,导师的名气也不是很响,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学到一些很实际、很有用的新东西,有助于回来开展工作。所以我选择了Eastmond。今天回想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做了一次很正确的课题选择。大家知道,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离开大学的学习,作为一个大学教师,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有机会,真正安下心来从事一点学习和研究,所以我是多么珍惜这个机会,这是可以想象的。在国外的两年我真是“如饥似渴”,学理论,打基础,做实验。然后到了1981年的春天,也就正好是我出国两周年的那一天,我就回来了。
回到复旦,我就面临着自主的选题。我当然希望继续研究“多组份聚合物的物理化学”。很巧,当时遗传所刚进口了一台非常好的 Hitachi 电子显微镜,这对我研究多组分聚合物的形态非常有利。同时我们教研室有几位老师,在HIPS, SBS等方面都在做工作,有一个比较好的做多组分聚合物的氛围。所以我就决定以多组分聚合物的物理化学作为主要的方向来做。那么具体做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我在国外已经考虑过,在阅读文献的基础上,我有了一些想法。就是关于block polymer和homopolymer,嵌段共聚物和均聚物的相容性的问题,我对它很有兴趣。 block polymer含有A和B两种嵌段,它和均聚物的A或者B放在一起,是不是相容,这个问题非常有高分子特色。因为你想,均聚物的A和block A,它们化学上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从我们传统化学的观点来看,它们不存在相容不相容的问题。同样的东西当然无限相容。在高分子中就不一样了。嵌段共聚物本身形成微相分离,那么你再将一个homopolymer加进去的时候,就牵涉到熵的变化,它就不会是无限相容。这里大家看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日本京都大学的Hashimoto和Inoue,发表在1970年,当时他们还是学生或博后,现在早已是日本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他们发现这个相容性不是无限的。但是只要homopolymer的分子量比block要低的话,它就会相容,溶解度非常非常大。但与此同时,我的老板在英国做的工作,用的聚合物叫ABCP,比较复杂结构的高分子。它里面最简单的部分,是H型的。两个A链,当中一个B链把它们连接起来。他用这个ABCP再加均聚物A进去,发现溶解度非常小。所以他认为通常情况,homopolymer与block polymer由于不利的熵的效应是不相容的。这两个观点实际上是对立的。不过很有趣的是他们在文章里并不辩论,而是各讲各的。这在科学文献上是常见到的,如果我做的结果和别人不符合,不一样,而且也没有办法来说服别人,那么我就先把我的结果发表了再说。但是我仔细的看了两方面的文献,我觉得这里面是有很清楚的分歧,原因虽并不清楚,但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们用的copolymer的architecture不太一样,所以可能会有影响。今天我体会到,文献上的分歧很可能就是一个新的生长点。当时我下决心弄清楚这个问题。我利用我们合成上的长处,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architecture的高分子,我们可以做比较。所以首先我们就做了很简单的接枝共聚物, poly(butadiene)为主链,带1-2根polystyrene支链的接枝共聚物,它的architecture很简单。我们发现,当加入均聚物的分子量很小的时候,溶解度非常大,所以基本上支持了日本学者的结论。但是不能就此满足,我们还可以做更加复杂的,所以我又做了和Eastmond 一样的ABCP。他用的ABCP加上和主链一样的均聚物A,而我加入和支链一样的均聚物B,就发觉它的溶解度也是非常非常小。接着我们做multibranch graft,就是主链上带了很多支链的,然后再加和支链相同的均聚物进去,结果溶解度也很小。综合分析这些结果,就会发现,凡是溶解度大的,都是共聚物的architecture,就是构筑很简单的。凡是溶解度小的,都是共聚物构筑很复杂的。所以实际上就存在一个block copolymer的“architectural effect”。到这时,这个问题的基本结论已经有了。但是要使它更有说服力,必须要拿出更过硬的证据。那么我们就想到了用阴离子聚合的方法,因为阴离子聚合可以得到结构确定的共聚物。我们合成了两嵌段共聚物,三嵌段共聚物,和四臂星型共聚物。它们的化学组成完全一样,只是architecture不一样,看它们和均聚物的相容性。这工作是我的第一个硕士生曹宪一做的,他非常非常的勤奋,真是个拼命三郎,。他在硕士期间就做了这样好的工作。他比较了这三种共聚物和均聚物的相容性。对于两嵌段的,溶解度非常大;三嵌段就低得多,到了四臂星型,溶解度就更小了,非常的有规律性。所以,综合了所有这些结果,我们就提出了相容性的共聚物architectural effect效应,也就是说,共聚物的构筑architecture越是复杂,它们形成微区的时候构象限制就越大,因此和均聚物的相容性就越小。后来还做了一些统计力学理论工作,使实验结论得到理论支持。这样,我在91年的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上发表了一篇评述文章,综合报道了这些结果。在87年得到了中国化学学会高分子基础研究王葆仁奖,还有89年国家教委的科技进步二等奖。这个王葆仁奖只有300元奖金,但是我还是很珍惜的。这是用高分子界的老前辈,也是我国高分子科学的创始人之一的王葆仁先生生前捐献的1万元建立的。大家也许觉得可笑,1万元可以建一个奖?但是这在当时还是很不容易的,王先生是用他的稿费捐献的,这是一个义举。不过很有趣的是,我想我对王先生的这个奖还是有“回报”的。怎么这么说呢?王先生和我是同乡,我们还是校友,都是扬州人。他的墓地,非常巧,和我的父母亲墓地是毗邻的,他们在另外一个世界做邻居了。我每次回去给我父母亲扫墓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忘记给王先生三鞠躬。这也算是“回报”吧(笑声)。这项研究工作做完以后的这些年来,你们查文献就知道了,还是得到了很好的反响,比如像美国的Texas大学做Blend的权威Paul教授,在89年的工作里就大段的引用我们的工作,并且指出他们关于PPO和SBS的实验结果完全支持我们的结论。应该说回国以来的第一炮打的还是比较响的,初战告捷。这也促使了我的研究风格的逐步形成,怎样一个风格呢?我想就是要在高分子物理和高分子化学两者之间的结合上下功夫。我不是真正高分子合成化学家,但是为了高分子物理化学研究的需要,我们可以自己合成我们所需要的高分子,用来做进一步的研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空间。
好,谈谈下面进一步做些什么事情。在80年代中后期,有关嵌段共聚物相容性和结构的研究,国际上有非常好的工作出现,如日本的Hashimoto教授等等,主要用中子散射和X散射的方法,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提到定量的高度上。这对我们说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先进的仪器,理论上的准备上也是不足的。所以这时候硬要和这样的强手去拼搏,也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与此同时,我注意文献的调查,我发觉在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新兴方向,就是在高分子共混物中通过引进特殊相互作用,特别是氢键作用提高相容性,是一个诱人的方向。当时看到了美国Brookly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的T.K.Kwei等人做出的工作,他们把聚苯乙烯里面引进了一些含羟基的单元,只要1~2%的含羟基单元引进去以后,它就和PMMA等聚甲基丙烯酸酯类形成氢键,就可以使两者由不相容转变到相容。我觉得就我们的水平来讲,做这类工作是很实际的。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高分子,通过改变它的组分把氢键引进去,改变引进的氢键的浓度。同时我们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特点,因为他们只用了一个DSC来表征,很不全面的。而我们的透射电镜已经掌握得比较好了,所以完全可以发展。另外我们也开始做荧光标记光谱法,所以就可能通过几个方法的综合,把这个问题做得更深入一点。所以选了这个课题。这课题的总的思想,应该说还是从外面文献上借鉴来的。这个课题开展得也是比较顺利的,对多种体系,用多种方法证实了同一个结论,即很少量氢键基团的引入就可以把不相容变成相容。但是,这样也只是对文献已有工作的延伸和拓展,没有太多创新的东西。真正创新的东西源于后来荧光光谱方法研究的结果。在两个不相容高分子共混物A和B里面,我们分别引进荧光的给体和受体,donor和acceptor。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它们不相容的话,donor 和acceptor不能接触到一起,那么它们之间荧光能量转移非常的小。如果共混物从不相容转变到相容的话,这能量转移就会有一个跳跃,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上。我们确实发现,只要成氢键的基团达到1~2%的时候,就会有个突跃性的增长。如果我们到此为止,说荧光光谱的结论跟TEM,DSC是一致的,那也可以“交差”,也可以发文章了,但这样我们就会失去下面的更精彩的文章了。当时我的硕士生陈文杰做了很好的贡献,我们不满足于看到当羟基含量到2%时达到完全相容,而是要问,如果再增大羟基含量会怎么样?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做到含量8%,10%,20%….就发现,到了5~8%这个范围,另一个新的突跃产生了,也就是说这个能量转移,比相容体系还要高。就是说在这样的共混物体系里面,两种链之间的接触程度已经超过了miscible体系, “more miscible than miscible”,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新的物理状态。为了证实上述实验是完全可靠的,我们又做了另外一个体系,得到完全相似的结果。于是我们就在Polymer上作了报道,提出,当氢键密度很高时,可能有物理交联结构,或链和链之间有结构互相配对。但实际上还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进一步大量研究文献以后,发觉文献上有多人做高分子络合物的研究,比如说PEO,它每一个链节上都有醚键,而PMAA聚甲基丙烯酸,每一个链节上都有羧基。如把它们的水溶液混合,这羧基上的羟基就会和醚键有氢键作用,每个链节和链节之间都有这样的氢键作用,所以两种高分子就形成“高分子络合物”,并从水溶液中就很快沉淀出来。很多人研究过这个事情。文献的阅读是对我们很大的启发。我想,虽然我们的体系不是每个链节上都有氢键作用基团,但氢键基团增加到一定程度,也很可能形成了高分子络合物,所以链间的非辐射能量转移就比一般的相容体系大的多。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个观点,我们做了大量溶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光散射的研究,有一部分工作是和香港吴奇教授合作的。对于溶液,做光散射,粘度,非辐射能量转移荧光光谱,也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研究本体状态的共混物。研究结果归结到一个共同的结论:在不相容体系中,随着氢键作用增强,会转变为相容体系,继而变为高分子络合物。也就是说,产生了不相容-相容-络合的转变。即所谓miscibility-miscibility-complexation transition。这样一个结论,实际上沟通了两个领域。为什么这么说呢?向不相容高分子中引入氢键作用,使它变成相容体系,这叫做氢键增容,很多人做过;但另外一方面,就是AB两种高分子,它每个链节上都各有氢键受体或者给体,它们在水溶液中会形成高分子络合物,也有很多人做。它们两个驱动力都是氢键,但是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竟然从来都是互不相干的,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而我们的结论说,这两个现象的驱动力是同样的,因而他们本质上是一致的,可以转化的,这就把这两个领域沟通了起来。我们就这个主题发了很多文章。特别是,我们在1999年在Advances in Polymer Science上发表了一篇评述,标题是“Interpolymer complexation and miscibility enhancement by hydrogen bonding”,题目就表明,这两者都出之于hydrogen bonding,这是我第二个阶段的中心工作。这些结论到现在都还很广泛地被这个领域的工作者所引用,很多人明确的讲,他们的实验支持我们的结论。这成果得到了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工作做到这个程度,便又面临新的挑战。我们当然也可以继续做下去,再选几个体系,看看它的络合行为,这样做当然省力,同学发表文章,毕业,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们应该把这工作从质的方面有所提高,有所发展。很巧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新的契机。自然科学基金委在九九年公布了一个重大项目的指南,要大家投标申请,标题是“有序高级结构聚集体的形成和构筑”,是涉及超分子化学领域的题目,它要求做的对象必须是“有序高级结构”,如果能够申请到这个项目,我们继续延伸和发展有关络合的工作就有希望了。乍看起来我们做这个问题是困难的。你们看,这里有A,B两种高分子,A链上有很多proton donor的基团,B链上有很多proton acceptor基团。当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一个高分子链A会和很多B链结合在一起,同时,一个B链也会和许多A链结合在一起。这样,势必形成一个无规的聚集体,这似乎是由它络合过程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要用这种体系来形成所谓regular structure,我们必须要有新的思路。在基金委发布这样一个项目时,我们确实已有一些新思路在脑海中形成,也有了很初步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大胆的去申请。这个项目我听说一共是有四十多份申请,经初步评审以后选了16份到北京进行口头答辩。而当时的这类大课题政策,就是要向年轻人倾斜,而我那时已经过了六十岁了,但是为了课题的发展,我还是得去跟这些年轻人拼搏一下。我内心还是非常重视这样一个答辩的,每个人的答辩时间为20分钟,为此我准备的时间,我想绝对不止20个小时,可能是40个小时或者更多,总之是逐字逐句的推敲。我在自己的研究小组里面预讲过2次,让我们同组的老师,让我们的同学为我算时间,提问题,纠正错误等等。最后我同十多位年轻科学家一起答辩。结果呢?从基金委同志那里我听说到一个非正式的评价:“姜还是老的辣”….拿到这样一个基金资助,就给我们99~03年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条件。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要通过polymer-polymer complexation 来得到regular structure。
说到regular structure,在高分子中研究得最深、最透的一种就是嵌段共聚物的micellization,可以得到核-壳纳米结构,我们不走这条路。通过几年努力,我们现在终于能够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不用嵌段共聚物,只用均聚物和无规共聚物,通过complexation的办法来实现这种结构了。怎样做呢?这里没时间展开讲,因此我仅举两个例子:
第一,我们还是用两种高分子,一种高分子主链上无规分布了很多proton acceptor的基团,而另一种高分子,分子量稍小一点,大约几千左右,重要的是通过合成的控制,将proton donor的基团只限制在它的端基上。当这两种高分子处在他们的共同溶剂中时,由于proton donor和proton acceptor的高分子产生氢键,就形成以含proton acceptor的高分子为主链和含proton donor的高分子为“接枝链”的“接枝聚合物”。然后,再把共同溶剂改变为选择性溶剂(主链的沉淀剂),主链就会沉聚起来。但是,由于氢键作用,聚集成的小粒子会连接着很多带有proton acceptor的高分子支链,由于这些可溶的支链的保护作用,不会形成宏观沉淀,会稳定住它,最终形成一个所谓的NCCM(Non-covalently connected micelles)。它的结构与嵌段共聚物形成的胶束非常相似的结构,但是它们有不同,NCCM的核-壳结构之间没有共价键的连接,只有氢键连接。这种NCCM是一种全新的高分子胶束,诞生在我们复旦大学。
第二,我们可以放弃将proton donor基团仅限定在高分子链的端基上的要求,我们还是用普通的proton donor A高分子和proton acceptor B高分子。不过我们把它们分别溶解在它们自己的溶剂里面,但是,B高分子的溶剂必须是A高分子的沉淀剂。然后把A的溶液滴加到B溶液,A就会沉聚下来,但是由于A和B之间有氢键相互作用,所以在A刚形成很小的粒子时,B很快就会向A的周围聚集。因为A和B间有氢键作用,而且B是可溶的,A的小粒子就被B稳定住,这样我们也得到NCCM。
还有重要的一点,在NCCM里面,核和壳之间是没有共价键连接的,这样我们就可能用简单的方法获得空心球。我们把NCCM的壳部分先交联起来,把胶束结构固定住,然后改变溶剂,使之可溶解核部分。随着核的溶解,并逐渐扩散出NCCM的壳层,最后得到空心球。空心球的一个优势就是它有很大的内部空间,可以装载(Loading)很多其它的东西。这里是一张我们的胶束的TEM图片,博士生窦红静得到的。大家可以看到这胶束的壳层和核部分界面非常清晰,核和壳的密度对比非常清楚,壳部分密度比较低,是相对比较疏松的堆积体。这些micelle的照片清晰、漂亮,最能反映胶束的核-壳结构。如果有哪位看到文献报道的micelle比这个更为漂亮,请告诉我,我似乎还未见到更好的。对这个胶束,在我们实验室称它为Miss Micelle,如果有世界micelle 小姐的选美比赛,我愿意送她去参加评比,可能不用包装就能够夺冠.(笑声)。这张是我们得到的空心球的图像,有非常清楚的外壳和内层之间的对比,文献中也少见,是江南大学刘晓亚老师在我们实验室得到的。
再有,我们可以用rod-like刚性高分子和比较柔性的高分子,通过氢键相互作用构建micelle,由于刚性链的自身平行排列的趋向,在它们的共同溶剂当中,它们直接就形成空心球,这个工作我们发表在JACS上面,后来又做了详尽的研究。这项研究还促成了我们组里的girl-boy self-assembly, 结合得比共价键还牢(笑声)。
以上的事实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不同的路线,利用化学的多变性,构建出很多新的胶束结构,空心球。最近我们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如,发展了很多在水相体系当中的空心球和胶束结构,它们是有环境响应特性的,显然这对于在生物医药方面的应用会大有好处。以上讲的这些路线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block copolymer free的路线,即不需要使用block copolymer。不过我们也没有放弃对block copolymer的研究,但我们不是简单地重复文献中在选择性溶剂中形成Micelle的路线,我们寻求更多新的导致micelle的路线。这就是陈道勇老师带领同学在研究的,小分子诱导的block copolymer胶束化,这也是很有特色的研究。另外一块就是姚萍老师带领同学,用了很多天然的高分子组合,有蛋白和蛋白的,蛋白和多糖的,让它们结合起来形成micelle,这种micelle由于组成都是天然的、无毒的,可以发展成为完全可食用的胶束,因此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第三阶段即“组装”阶段的工作,比较我们以前的,是大大的推进了一步,从创新性和系统性上看都上了个新台阶。
3. 幸福之源
从79年开始做科研,至今已二十五年了,在这二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总体来讲我是很乐观的,过得很愉快的。我和同学们说说我这种快乐和精神享受来自何处。第一个,就是我刚讲的,我充分享受到自由选题的乐趣。回顾科研工作多年,从来没有哪个领导直接对我的选题干涉过,不让我做什么或者指定我一定要做什么,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课题选择完全是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定的,也就是curiosity-driven,完全由“好奇心”驱使去做,从深究问题的科学内涵来提练出问题,去寻找自己想做的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最愉快的事情。不过,照这样讲的话,大家都只想做这类研究,很少有人去做开发性的研究,更少人去企业里去从事研发工作了。其实事情不会这样。这里牵涉到很多得和失的关系。是的,我们是充分享受到自由选题的愉快,但同时,我们也要失去一些东西。失去什么呢?与同资历的人相比,他们在工业部门,从事研究开发,他们的收入要比我们多得多。我的学生,即使是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如找到好的位置,收入也比我要多,在国外情况也是如此。但在那些单位工作,他是不能这样的自由的,他们从事的研究由市场决定,由领导决定。很急的时候,可能要加班加点把某项研究赶完,一旦发现市场不再需要了,老板也许会要求你明天就必须把它停掉,哪怕你对这个课题再有感情,你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之间可以做取舍。同学将来毕业择业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你对研究工作,对基础研究,真的有兴趣,在“业余”时间你愿意投入更多,那么你来做,就会得到很多幸福,但同时你也要准备失去很多东西。作科学研究是“没完没了”的,各种需要和新问题不断的出现,迫使你不断地学习,这样,你就必须要放弃很多,比如生活上的享受,你的业余的快乐,业余的休闲时间,都会损失很多。二十多年了,我的假日总是很忙,每次寒假、暑假开始之前心中早有了规划,因为这时同学比较少,比较安静,可以抓紧时间完成几篇文章。即使如此,我总是觉得有太多的知识要我去学,太多的事情等着我去做。
快乐还来自于所谓的成就感,从我刚刚讲的我们几个主要的科研阶段所做的一些事情,大家也许已能体会到这一点。当然还有一些项目我没有讲到。比方说,我们还做过水溶性高分子的疏水缔合的问题,也就是在水溶性高分子链上引进少量疏水基团,这疏水基团在水相中会缔合起来,从而产生一些很有趣的性质,我们与章云祥老师合作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们是用碳氟链来修饰水溶性高分子的,必须要测定和表征疏水微区的形成。用荧光光谱的方法,即用Pyrene来做探针是很方便的。一旦微区形成,Pyrene就会进去,荧光就会有很强的效应。别人对碳氢微区的工作已经进行了很多,所以我们也用这个方法来做。但是发现不行,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说明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很快就想到了,pyrene虽在碳氢微区里能够很好的溶解,但可能不能在碳氟链的微区内溶解。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是化学家,我们很容易想到,在这个pyrene上接上很短的碳氟链。这个工作从有机化学的角度来讲,很容易做到。用这个碳氟链修饰过的pyrene来做探针,问题就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结果发现可以显示很好的荧光效果。李梅做了相当完整的数据,变化了好多条件,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很难解释的东西,特别是它接上碳氟链以后在有机相里面的一些荧光表现,很迷惑不解。为写论文,我就一个人闷在家里,大约有十多天,完全集中精力和时间来钻研这个问题。看了大量的相关文章,逐渐了解和领悟了难点,直到豁然开朗了,把问题都解释得清楚了,便一气呵成地写完一篇长文章,最后这篇文章得到Macromolecules杂志referee的很高的评价,对四个指标全部给出了“excellent” 的评分。这篇文章迄今为止是我单篇文章SCI引用次数最高的。特别是,我们发明的这个探针已被法国,日本的实验室相继应用,用在各种不同的含碳氟链的微区体系里面,都得到了成功。这不是一项很复杂的研究,但成果很实在,老外也跟着用了,这当然给我带来特别愉快的心情,可能这是从事其他职业的人难于享受到的一种快乐。
再有,我想我的快乐还来自于真诚的合作。我们有好几次很成功的合作,包括早期在均聚物和共聚物的相容性方面,我们和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谢涵坤老师的合作。他是搞理论物理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共聚物和均聚物相容性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水溶性高分子疏水缔合问题,我和章云祥教授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做了一些分工,合作也是非常的愉快。跟吴奇教授的合作就更多了,我们一起合作了十多年,我们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在去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很有趣的是,我们合作很多年,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合作的课题,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课题是共同享有经费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它驱使我们在一起来作研究,我们从来没有为成果的分享产生任何的隔阂。在我看来,我们是搞科学的,应是客观的,也容易对自己在合作项目里的贡献的大小有个科学的客观的判断。然而不成功的合作总常常出现,很多是由于为了某种目的,想夸大自己的贡献。如果大家都真正客观地对待的话,合作总是互补的,总是相互有利的,也就不会出现不愉快。不过,客观地讲,现在的一些评价体系是很有问题的,什么“第二单位的贡献不算”啊,“第二作者的贡献不算”啊,这样大家都抢第一单位和第一作者,那怎么会合作得很好?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要在这儿讨论的话题。
接下来我想说,愉快的心情还是来自于和同学们多年来的相处。这里列出的是历年来我组已取得学位的同学的名字,包括谢静薇,陈道勇和姚萍老师培养的同学。我们和那么多硕士生,博士生同学相处过,他们在研究工作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上所讲的成果,都是由他(她)们做出来的。多年来我和一批又一批得同学们相处,在一起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这样也促使我努力地去思考。所以即使我现在到了六十多岁,我还能保持一种比较年轻的思维方法和状态来考虑问题,我觉得这是因为受到同学们的感染。我的老同学们,同龄的老同事们都已经退休了。如今和他们在一起谈到的,主要是几个主题,保健,就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健康;旅游,就是如何玩得开心;还有就是孙儿孙女的趣事,天伦之乐。跟同学在一起就不会谈这些了,同学会不断地提出科学上的问题,希望我们一起去探讨,去解决。接触了这么多的同学,他们的能力是有高低的,性格也有差异。但总体上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青年,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到复旦来学习,走科学的道路,所以是一个优秀的群体。跟同学们相处,共享研究的成果,确实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事情。近年来我还不断从他(她)们那里得到好消息。张广照和刘世勇在中国科大当上了“百人计划”教授了,杨澍和祝磊在美国当Assistant Professor了,徐世爱在华东理工大学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还有更多的在企业界做得很好的。再有,有人提职了,买了新房子了,生了胖儿子了,也没有忘记让我分享他们的快乐。
关于我为什么能保持快乐,我讲了许多,但似乎忘了讲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我见证了我们国家这20年的巨变,伴随他从深渊中挣扎出来,一步步迈向光明。见证了我国的化学研究从世界垫底到今天成化学论文的世界第三大国,也为此流了汗水。这是真正的幸福之源。
4. 经验之谈
再回到关于课题选择的问题上来,我想,总结几条就是:
首先,我们要做到“借鉴联想,为我所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联想集团的广告语是,没有联想就没有世界,实际上我觉得没有联想也没有好的科学研究。我们的同学们所学习过的基础知识,都是差不多的,但是为什么有人做的比较好,有人做的就不是那么好?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是否拥有借鉴联想,灵活运用的方法和能力。从大的方面来讲,很多很重要的研究,大的成果,是通过借鉴和联想得到的。最突出的就是ATRP,这可以说是高分子合成中革命性的成就。它就是把有机化学中的原子转移反应移植到高分子聚合反应来的结果。再如我刚刚提到的Morawetz,他就是最早用荧光标记的方法来做高分子相容性的问题的,其实用荧光标记,非辐射能量转移研究相互作用并不是他的首创,这个在生物科学里面,已经用的很多了,他就是借鉴了这个成果到我们高分子学科来。还有,高分子电子显微镜研究当中,日本人Kato首先把生物上用得很多的四氧化锇染色方法用到高分子上来,后来得到了极广泛的应用。在六七十年代,他文章的引用率我想要上千篇。而我们在自己工作中,有几次转折得比较好,有比较好的发展,和这个借鉴联想也有关系。例如说,我们发现共混物非辐射能量转移,随着氢键作用的增加,出现第二个跳跃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认为,这说明相容性变得更好了,异种分子间的接触机会更多了,而不再深入想下去,那就没有以后的精彩故事了。可是,我们联想到别人在高分子-高分子络合领域的工作,虽然他们作的体系跟我们做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的思路就拓开了,“柳暗花明又一村”,这才出现了后来发现的“不相容-相容-络合”转变这样一个重要的结论。所以我想同学们要在这方面多花功夫。
第二点就是“抓住疑点,捕捉光明”。很多重要的结果都是在解决所谓的不正常,异常和矛盾当中发现的。在我讲的第一个研究课题里面,共聚物和均聚物的相容性,我之所以做这个工作,就是看到一个疑问,就是文献上两家著名的实验室的结果有不同,虽然他们自己“和平共处”不去争论,但我们看到这个疑点,然后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捕捉到光明。再有个例子,就是有关刘璐的发现的。离子化程度非常低的高分子,我们叫离聚物,像聚苯乙烯或聚异丁二烯,如只含有1%的羧基,在有机溶剂里面是可以溶解的。为了纯化高聚物,把它滴加到水里面去。因为聚苯乙烯是典型的疏水聚合物,以为它马上会沉聚下来。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出现了微弱的蓝色乳光,形成了几十个纳米左右的粒子,这个现象就是疑点。我们没有放过,继续深入做了几年。做各种各样的离聚物,各种条件我们都去做,特别是借用光散射这样一个手段,深入地做。这样,我们就把一个偶然发现的现象上升为一个普遍性的规律的东西,也就是“微相反转制备无皂纳米粒子”。这就是“抓住疑点,捕捉光明”的做法。
第三,可能讲得更大一点,有些像政治家讲的了,叫做“继承传统,与时俱进”。大家可以看看,我讲的工作的三个主要阶段里,后面的都是跟以前的有联系的,研究新的东西时,我们不是完全放弃原有的东西,样样都另起炉灶,而是一步步发展,有继承的关系。与时俱进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讲,更需要强调,你们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已经具备了比较好的物理的、化学的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在我们现在交叉学科迅速发展的情况下,更要有勇气与时俱进,拓宽自己的领域。现在高分子发展特别依赖于生命科学和高新技术的需求,因此有很多东西需要你们去学,需要你去探索,要有这个勇气去探索,与时俱进。我有这样的信念:在你们这样的年龄,应该说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东西。
讲到这里,应该要结束我的讲话了,那么怎样结束呢?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我办公室里的一幅瓷屏,一幅书法作品,上面写的是“山间明月,江上清风”,是吴奇教授赠送的,因为他看到这里面有我的名字嵌在里面。这句话取自苏东坡的“前赤壁赋”,我体会到这是一种意境,很优雅的意境。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到的,当你花了很大力气,攀登了很长的路,克服重重艰难,最后成了,好文章刊出来了,别人引用了,同行赞赏了,你当时的心情不就达到了山间赏明月,江上浴清风,这样的意境了吗?
想不到一口气讲了那么多。你们齐聚一堂,全神贯注,甚至许多同学站着听到现在,这让我兴奋起来了。谢谢同学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