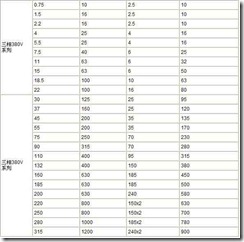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之后,捍卫西方秩序和价值观的责任就落到欧洲大陆肩上了。
11月20日,欧洲大陆最重要的两个国家法国和德国同时发生了世界瞩目的政治大事件:法国前总统、共和党主席萨科奇党内初选被淘汰;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沉默数月后宣布竞选四度连任。
对今年以来屡被重击的西方来说,这两个信息是少有的好消息。萨科奇被淘汰,增大了传统政党击败极右政党的可能性,后者乘脱欧和特朗普之胜意欲冲击总统大位。而默克尔仍然是迄今为止德国支持率最高的政治人物,她的出马将有助于稳住岌岌可危的西方局势:假如欧洲再被极右民粹领导人物掌控,整个西方恐将难有宁日。
以本人对欧洲的观察,至少在选举上,法国和德国都有可能保住西方最后的防线,但是否能够拯救西方则是另一回事。
法国之所以能够顶得住极右政党国民阵线的挑战,原因有二。
法国的国民性
一是法国的国民性。纵观历史,法国这个国家不到撞南墙的一刻是不会醒悟的。远的例子不说,二战之后,民族英雄戴高乐鉴于第三共和的动荡和无能,提出修改宪法,强化总统权力。结果却被否决,以至于戴高乐不得不辞职,赋闲在家十余年。直到第四共和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军事政变、镇压政变的武装力量倒戈、民众游行抗议席卷全国、财政破产靠全球借债度日、国家完全失控。此时,戴高乐才被重新启用,并被授权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把法国从动荡中解救出来。
今天的法国虽然问题不少:长期经济增长低迷、失业率高企、债务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100%、贫富差距扩大、治安严重恶化、恐怖袭击常态化。但仍然没有严重到山穷水尽之时。一方面法国仍然能在全球以较低成本融资,另一方面经济增长期间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崩溃,简而言之,老百姓只是强烈不满,但还没有到必须革命的程度。
——这一点和盎格鲁萨克逊的英国、美国不同。不管英国脱欧和特朗普上台对西方冲击、否定多么猛烈,但这两个国家确实很敏锐地对挑战做出了迅速而决绝的反应。对于英国而言,虽然代价沉重,但至少减少了主体民族和信仰受外部冲击的风险。其实早在退欧之前,英国首相卡梅伦就已经公开冒天下之大不韪,宣布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留欧派都是如此观点,脱欧派可想而知。特朗普是否能够解决面对的挑战还需要时间检验,但至少提供了改变的可能性。
浪漫的法兰西民族好享受,小资情调浓厚,对危机反应迟钝,不到最后绝境时刻无法改变。这就是传统政党仍然可以胜选的决定性背景。
法国“科学”选举制
第二则是法国“科学”的选举制度。法国几乎所有的选举都是两轮制:不管是议员、大区还是总统。第一轮如果有人直接选票过半就直接当选,如果不过半,前两名得票最高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由于政党和候选人众多,一轮直接胜选的可能性极小。而一旦进入第二轮,传统左右两大政党就可以联手绞杀极端势力。2002年,极右的国民阵线候选人勒庞击败传统左翼社会党进入第二轮。结果左右联手,令右派的希拉克获得罕见的80%以上的支持票。2015年法国大区选举,第一轮“国民阵线”在13个大区中的6个大区均处于领先地位,但在第二轮却全军覆灭。这和社会党为了遏制“国民阵线”的势头,宣布在“国民阵线”领先的几个大区,支持率处于第三的社会党候选人自动退选直接相关。传统左右政党不是通过民意战胜了极右,而是通过算不上公正(当然合法)的选举手段。
假如法国采用台湾一轮选举制度,那么2017年极右政党获胜的可能性极大。事实上,连续四年来的选举:不论是国内选举还是议员选举,极右政党得票率都是第一。
相对于美国落后的选举人制度,法国模式不仅形式上更民主——是唯一民众可以直选国家领导人的西方大国,在遏制极端势力掌握权力上效果也更佳。
至于议会制德国,在难民处理问题上备受指责的默克尔胜选的机会仍然很大。一是由于历史原因,德国举国上下十分警惕并反对极右势力,极右势力在德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也长期缺少成长空间。这和法国极右势力长期存在,并有稳定且不断增长的支持是不同的。
二是德国选民并不能直接选举总理,而是由选出的议员投票产生总理。一般是哪个政党赢得国会最多席位,哪个政党的领袖就能成为总理。相对于法国极右只要推出一个领导人就有可能赢得大选不同,德国极右政党必须推出数量众多的候选人竞选议员,而且必须还要赢得国会多数才能统治这个国家。发展历史并不长的极右势力推出一个候选人不难,但要推出如此之多的候选人则十分困难。毕竟人才的培养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所以德国极右可以赢得比过去多得多的国会席位,但却无法达到过半,哪怕默克尔的政党也过不了半,但她却可以和其他传统政党联手。就如同现在,她就是和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
欧洲能拯救西方吗?
然而,法国、德国传统政党虽然可以赢得大选,但却无法拯救西方。根源在于传统政党无法解决面对的挑战。
法国无论谁上台,都需要进行必要和痛苦的改革。但目前民众没有撞到南墙,不认可改革,那再好的制度只能以失败告终。二十多年前,希拉克一上台就要进行改革,却引发抗议示威,导致整个国家瘫痪。自那时起,没有哪个政治人物能够改革这个国家。哪怕是2008年的经济危机,哪怕是现在第一轮得票率最高的菲永——他在任总理时坦率承认法国国家财政已经破产,结果却引来一片责骂声,大众拒绝面对现实。
所以传统政党执政的后果只不过是推迟危机的爆发并让危机继续积累到极其危险的程度。到了那个时候,法国就只能两种命运:一是传统政党出现强人,比如当年的戴高乐,一是极右政党席卷法国。只是今天的法国已经不是二战后的法国了。那个时候法国还有战争期间建立起威望的戴高乐,法国也没有极右势力——极右势力都已经随着纳粹的毁灭而走进历史。但今天法国传统政党已经没有崇高威望的强人,极右势力早已在法国建立起雄厚的实力,只要那一刻来临,极右上台几乎是铁板钉钉的事了。到了那个时候,代价将更为高昂。
德国和法国不同。德国这个民族务实理性,政治人物也更有魄力和牺牲精神。2000年之时,施罗德总理就进行了痛苦和不受欢迎的改革,哪怕下台也不改初心。默克尔上台后,也是继续坚持施罗德不受欢迎的痛苦改革。再加上德国人勤劳、储蓄率高,德国经济是整个西方最好的。
也就是说德国的问题不是在经济,而是在种族和价值观——法国也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经济是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务罢了。
根据出生率,法国和德国将很快面临中东裔人口暴增的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默克尔却迅速的决定接受一百万来自叙利亚和利比亚以穆斯林为主体的难民。这个决定为极右派在德国的迅速崛起创造了条件。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批评默克尔此举将毁灭德国。
确实从人道的角度,每个国家都应该对难民伸出援助之手。但前提条件是这个国家得有这个能力,而且不能影响到本民族的未来存亡。但显然在默克尔看来,价值观和理想高于一切。所以只要是默克尔执政,德国就不可能象特朗普一样,会遣返非法移民。当种族问题随着出生率的差异而继续激化,随着默克尔的政策而日益严重,当达到临界点时,救亡图存必然成为德国民族的首要任务。在这个时候,传统政党就必然被抛弃,而极右政党势将登上历史舞台。
当德国极右势力成功之时,经济问题和种族问题同时爆发的法国也无法独善其身。欧洲不但不能承担起拯救西方的历史任务,相反还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说,2017年法国和德国传统政党赢得选举,只不过把危机延迟爆发。至于危机有多严重,不妨听听西方自己的声音。当特朗普胜选时,一份德国报纸惊呼“啊!我的天呀!”,还有一家干脆说“我们在沉痛哀悼”。《德国之声》则惊呼这是划时代的灾难。另外一位德国部长形容美国大选结果是“我们醒不来的一场噩梦”。英国《金融时报》的文章则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无异于《现代启示录》成真”。美国的媒体则早在选举之前就把特朗普和希特勒划上了等号。著名的学者福山则说:“选了特朗普,民主做为美国象征也告终”。
今天的西方,很像1976年的中国,原来的模式已经不可持续,必须进行痛彻心扉的改革。但不同的是,当时阻碍发展的价值观如绝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等都不是中国文明的产物,而是学习苏联的结果。所以中国仍然有能力在不影响自己文明的前提下进行一百八十度的变革。但今天阻碍西方发展的价值观都是西方文明内生组成部分,根本无法切割。如果西方不能自我变革,不管世人是叹息还是兴奋,都改变不了这一颓势。如果将来的人类回顾历史,将会永远记得2016年和201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