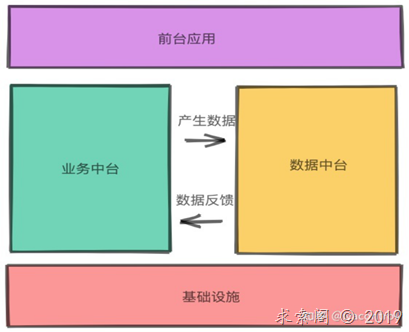中国正处在其历史上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崛起期,而这也同时是亚洲的崛起期。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促进这一活力向亚洲的扩展,追求亚洲的连动发展,成为这一地区有识之士热烈讨论的主流话题。今年早些时候在东京举行的“日中产学官交流论坛∶中国的大城市群与东亚经济圈”上,来自中日两国的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与展望。
亚洲经济进入连动发展时代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1/4世纪里,实现了平均9%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其结果是,中国从一个封闭贫穷的国家跃进为仅次于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位贸易大国。GDP的规模也跃升为世界的第四位。2005年贸易顺差首次超过1000亿美元。GDP首次超过了2兆美元。
东京经济大学周牧之副教授认为,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从结构上看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是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基础上的大分工、大交流型的发展,特别是与东亚区域内的分工非常密切。东亚各国分工的深化导致东亚区域内贸易率从1980年的34%上升到2004年的55%。
第二个特征是中国经济增长极的巨大化。从地理上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中国经济今天正在向大城市群急剧地集中。2005年三大城市群创造了中国GDP的42.4%和出口的77%。
第三个特征是大规模利用世界资源。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能够获得利用世界资源的国际环境。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以三大城市群为中心,利用世界资源的规模正在急剧地扩大。例如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始于1981年,到2005年其规模已经达到了27,500万吨。近年石油的进口也在剧增,2005年达到12,700万吨的规模。对世界资源的大规模利用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虽然进口了大量资源,但是中国的人均能源以及铁矿石的消费量还很低。中国对世界资源的进口今后还会持续增长。
日本今天的经济结构有着与中国经济相似的特征,而且中日经济正在不断地深化分工和合作。2004年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成长的中国市场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因素。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也在中国创造了超过1000万人的工作岗位。
周牧之据此认为,中日经济已经进入了互相依存的时代,中日两国的经济都在从以国民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向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开放经济进行转型,“鸦片战争以后亚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不断降低,直到今天亚洲才重新开始增大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在这背后亚洲各国经济的互相连动和分工合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长、日本综合研究所会长寺岛实郎很认同周牧之的观点,他列举数字说,2004年亚洲占世界GDP的比重是24%,综合许多资料可以预测,到2030年亚洲占世界GDP的比重将超过50%,“在1820年,中国、日本和印度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超过了50%,也就是说,在这以后的近200年,我们经历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两百年后的亚洲正在重新向超过世界GDP50%的时代复苏。”
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先生曾提出著名的“雁行模式”:即把亚洲国家的发展比喻成大雁的飞行,以日本为领头,其次是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东盟等依次梯队发展。
寺岛实郎说,过去有很多日本企业接受了这一理论,制定了从东京放射状看亚洲的经营战略。但是现在日本企业大多认识到亚洲今天进入的是一个连动发展的局面。日本领头牵引亚洲经济发展的认识是一个错误。中国、印度、东盟各国都有着各自形态不同、大小不同、性能不同的引擎,牵引着经济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各国发展互相连动,所以今天的日本企业在中国设厂时,已经不再是用如何从日本的本社提供零部件这种思维来设计它的供应链,而是进入了以在中国的工厂如何实现最恰当的零部件供应、最恰当的市场供给为核心的发展阶段。”
寺岛实郎提出了一个“大中华圈”的概念,其所指包括中国的大陆、台湾、香港和华人人口占78%的新加坡。日本目前对大中华圈的贸易比重高达28%,而对美贸易比重不到18%。他说,日本现在陷入了头脑和身体分离的状态。所谓的身体也就是日本的下部构造已经进入了与亚洲,特别是与大中华圈不可分割的时代。但是脑袋,也就是上部构造的90%以上还是偏重与美国的关系。虽然日美关系很重要,但如何深化与亚洲的有机连动是日本的重要课题。目前日本的脑袋处于昏浊的未整理状态,而身体却已经发生了质变。这使日本迷失了对未来的方向感。
繁荣和紧张的亚洲海洋
中国经济的三大引擎—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这三大城市群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们的对外开放性。周牧之说,历史上中国也曾经出现过对外开放的大都市,例如唐代的长安,作为丝绸之路出发点的长安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世界都市,然而在唐朝灭亡以后的一千多年漫长岁月里,中国选择了自我封闭。今天中国出现了面向海洋的开放的巨大城市群,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它对亚洲的经济政治格局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人们都希望把东海变成和平的海洋,但实际上今天的东海仍存在包括领土纠纷,石油、天然气等海洋资源开发争议,安全方面的相互戒备等许多危机。朝日新闻社特别编辑委员、专栏作家船桥洋一说,“这些问题起源于这一地区国家在自己的发展战略中对海洋以及海洋资源如何看待所引起的磨擦。”
他说,中国和东亚各国和地区都是通过利用海洋而发展起来的。1970年代的“四小龙”是如此,1980年代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也是如此。在东盟加日中韩这13个国家中,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只有老挝,其他国家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都面对着海洋,历史上的发展都与海洋息息相关。
中国的大城市群就是建立在这种对海洋依存的基础之上的。今天中国作为海洋国家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日本和中国都是世界上拥有岛屿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有12个省和直辖市面海。作为海洋国家,中国在宋代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明代永乐帝时期的郑和曾经进行过7次大远征。但此后中国突然进入了锁国状态,采取了海禁政策。受中国的锁国影响,李氏朝鲜、德川幕府的日本也相继采取了锁国政策。此后亚洲主要国家在没有创建海洋合作机制的情况下进入了21世纪。这就是亚洲海洋的现状。
船桥洋一介绍说,日本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创建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联合起来的海洋民主主义联盟。这种想法明显是针对中国的。他们认为中国是大陆国家,日本是海洋国家,是民主主义国家,而中国不是,所以应该分成两个阵容。
船桥洋一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对的。首先必须看到中国作为海洋国家发展的一面,同时还要看到,作为海洋国家的发展是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契机。对于中国而言,如何与亚洲各国一起来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然后通过海洋来加深互相的分工和合作,已经变得非常重要。这些对未来提高中国的海洋性和开放性有着重大的意义。
周牧之指出,亚洲今天进入了同时具有成长和紧张两个侧面的时代。可以说,中国从大陆国家向海洋国家的转型带来了亚洲的成长和紧张,“600年前,郑和曾经7次远航,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贸易圈。但此后的600年间,亚洲的海洋里失去了亚洲自己的交易体系。”
周牧之认为,中国重新回到封闭的内陆国家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亚洲需要营建区域内的海洋交易体系,但是这还没有真正开始。例如中国的集装箱港口虽然取得了迅猛发展,但是亚洲区域内的海运物流最需要的却不是集装箱船的运输。这点从日本国内的物流结构可以看到,日本的国内海洋运输用的都是装卸更加便捷的RORO船和汽车渡船。亚洲区域内的需要强化小量、多频度、高速度的海运物流,这样的物流体系在亚洲还没有能够实现。其原因与其说是物理的问题,不如说是国与国之间海运政策交流的问题。
原日本综合开发研究机构理事长、原日本经济企画厅次官星野进保说,并不是集装箱港口越大就是经济发展的象征。从日本的经验来看,港口最初作为出口港来发展,然后出口港再逐渐转变为原材料的进口港。从这种意义上来讲,产业结构的变化,直接反映到港口形态的变化。今天中国的港口作为原材料进口港的发展也非常迅速,但是如果中国的能源消费效率提高,原材料的进口得到抑制的话,中国港口的发展又会呈现另外一番景象。
“思考海洋是什么非常重要。”星野进保说,“从海洋资源上看,还有着很多未开发的领域。例如日本最近深层水的利用非常流行,把从深海里采取的水通过处理用在饮用、化妆等领域很受欢迎。从这个小小例子可以看到对于海洋的利用不应该仅仅是局限在捕捞渔业资源或者是通行船只,海洋还具有很多我们可以开发的资源。所以我赞成要一起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利用海洋资源。”
创建亚洲共同发展的机制
寺岛实郎说,亚洲的未来需要智慧的连动,尤其需要日中双方有头脑的人进行交流。因为在目前政冷经热的状态下,东亚共同体的现实性,以及在亚洲能否实现像欧洲那样的经济共同体,虽然显得很渺茫,“但是,如果在一个一个的课题上实实在在地互利合作,这些合作的累积将会成为未来亚洲共同体的基础”。
寺岛实郎还认为,如果能够形成亚洲的资金为亚洲共同利益循环的机制,将会对整个亚洲产生巨大影响。日中韩三国加起来的外汇储备超过了2兆美元,如果能够拿出其中5%来进行项目合作,将会有重大的意义。例如亚洲开发银行提倡的湄公河三角洲的开发;又如鉴于马六甲海峡的繁忙,现在中东石油的70%都被运往中日韩,而这些石油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因此可以构想开辟横断马来半岛的运河;再如,如何协助中国解决环境问题。实现这些对亚洲各国有共同利益的项目需要创造共同合作的机制。
船桥洋一说,1970年代在欧洲,北海、波罗的海、地中海的周边国家虽然分别属于敌对阵营,但却超越了这些障碍一起合作进行了海洋的环境保护,例如利比亚与以色列一起签署了《禁止地中海海水污染》的条约,苏联与德国等波罗的海国家共同制定了保护波罗的海环境的条约。
而在亚洲,这样的海洋环境管理制度的建立还刚刚起步。船桥洋一指出,东中国海、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都是世界级的渔场,如此丰富的渔业资源得惠于阿穆尔河和长江。阿穆尔河给海洋带来了西伯利亚森林的丰富营养。长江起源于青藏高原,把高原的冰雪最终注入东中国海,“在亚洲有着森林和海洋的循环,可以说森林是海洋的恋人,中日之间需要共同拥有这样的认识”。
船桥洋一还说,日本曾经出现过由海洋污染引起的水俣病。当时被污染的海洋过了50年才得到恢复。经历了高度增长造成环境污染悲剧的日本,如何将自身的经验教训告诫给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们,应该是日本的责任。
而对中国而言,如何与亚洲各国一起来开发海洋,保护海洋,然后通过海洋来加深分工和合作,已经变得非常重要。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计划司司长杨伟民认为,要真正地保护海洋,必须对流入海洋河川的上流进行环境治理,“例如在中国的三江原地区,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已将这一地区列为禁止开发地区,以此来保护黄河、长江源头地区的植被和水资源,防止泥沙的流出。这种限制开发的构想不仅是为了保护内陆地区的生态,更是着眼于保护海洋的环境。”
谋求新的发展模式
杨伟民说,今天的东亚进入了一个非常繁忙的时代,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只要工作8个小时就可以回家了。但是今天的中国人要工作得更多,中国的大城市群今天成长为世界工场,每年中国要给60亿的世界人口每人生产一双鞋,每人生产两米布。为了持续这个世界工场,中国人必须辛勤地劳动。
但是也可以考虑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比方说西班牙人上午10点上班,下午1点到4点午休,然后黄昏时早早下班,去看斗牛,去听音乐。即便这样,西班牙的经济也取得一定发展。
因此,杨伟民认为,中国需要考虑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发展什么样的产业。
“中国还能不能够继续今天的发展模式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今天全世界的钢铁、水泥等工场都在向中国转移,这种工场大转移在中国造成了大量的能源消费和污染排放。中国人为此拼命地工作,生产出大量物资供应世界。”杨伟民说,“但我不认为这种模式能够持续下去,今后需要重新考虑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分工体系。各个国家和地区都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对这一点各个国家需要协商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