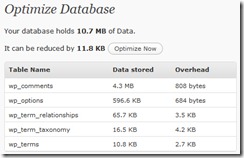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尽管前途未卜,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已经有很多经验教训可以总结。有人用民主化运动来形容这场运动。这场运动有争取民主的因素,但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走向民主化的开始,还需要观察。人们不满于旧体制,想推翻旧体制是一件事情,而能否建立一个新体制,这个新体制和旧体制有什么样的关联,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发展中国家不仅应当关切这些国家会往何处走的问题,更需要思考这场运动为什么如此有效。鉴于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很多参与者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社会成员,这里想着重讨论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社会政治所能产生的影响,想说明的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不能和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那么就会产生无穷的政治后果。
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在以往很多年里,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但是培养出来的人学无所用,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处于失业状态,就业不足,而新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他们所受的教育赋予他们很高的社会期望或者期待,但当他们的期望不能得到有效满足的时候,就演变成失望,最终是对政府和政治的怨恨。在这次运动中,受过高等教育者充当了“革命”的主力。
中国的情况不像埃及那样严重,但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脱节方面,非常类似。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城市高等教育大扩张,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都能容易地进入高等教育系统,但同时因为教育的产业化,国家又没有比较好的针对农村人口的教育政策,很多农村学生没有财力进入高教系统。这样就产生了很多负面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结果。
文凭“含金量”减少
首先是文凭“含金量”减少。因为高教的大扩张,得到高等教育文凭的人越来越多,但文凭的附加值则越来越小,甚至是负面的。现在,高中生的工作被大学生抢走,大学生的工作被硕士生抢走,而硕士生的工作被博士生抢走。在中国还得加上博士生的工作被博士后抢走。这样的情况可以概括为“高文凭,低就业”。其实,这种情况还好。更为重要的是,大学生不能找到有用的工作。一方面是企业找不到有用的人才,而自诩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高等教育系统,其毕业生则找不到工作,导致大量大学生失业或者大面积的就业不足。在很多地方,大学生往往要和农民工竞争工作,而且竞争力不如农民工。这实在是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嘲讽。
再者,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中,来自农村的人口越来越少。这不仅仅是因为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农村学生不能接受和城市学生同等的教育;更是因为价格越来越高的高等教育,把那些学业优秀的农村学生排挤在体制之外。这不仅在加深着中国社会的不公平性,也经常使得这个被排挤的社会群体越来越具有政治性。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这里的原因很复杂,但有几个因素非常显然。
首先是高等教育决策者对人力资源投资的片面理解或者错误理解。从1949年以前的“教育救国”到当代的“科教兴国”,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人一直很重视教育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强化教育投资,尤其是高教投资。这便是高教扩招、大学扩张、大学升级的背景。但是,这里面的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对教育的投入到今天为止还没有达到GDP的百分之四,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很多的教育投入并不是从经济、社会、技术的发展来考量的,而是从政治稳定的角度。高教的扩张从哪里来?一是产业化,就是从社会获取大量的财力。在很多地方,大学已经成为大学就职者“寻租”的工具,也就是盈利的工具。(应当指出的是,从社会获取教育资源并不是高教的社会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办学还没有开始。)二是最便宜的投资,就是开办那些投入少而产出大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培养出大量的只有“说话”能力而没有“动手”能力的学生,导致了上面所说的“学无所用”的局面。
其次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政策协调出了大问题。高教改革由教育部负责,但没有和其他部门紧密协调。高教系统实际上变成为一个没有和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相关的独立的实体。在成功的国家,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必须和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人才并非抽象,而必须为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但在中国,教育系统更多是属于政治范畴,属于思想控制系统。很容易理解,由于权力部门的分工,管理这个系统的领导,其所强调的不是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概念,而只是想着如何控制。在很大程度上,高校的属性仍然是政治组织,和社会经济发展部门相去甚远。
GDP主义扭曲高教改革
教育部门的GDP主义更是有效地扭曲了高教改革的目标。GDP主义先在经济领域盛行,很快就传播到教育部门。在经济领域,衡量党政官员政绩的指标是地方GDP的增长。延伸到教育领域,大学的规模和级别,毕业生的数量,教员所发表的论文数量、所申请到的各种基金、所指导的学生数量等等,都成为衡量一个大学好坏的“科学”指标。因为所有这些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和金钱有关,GDP主义就为大学的每一角色予巨大的动力和动机来追求数量。学生质量及其和社会经济的相关性则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中国社会也能够容忍这种情况。在文凭传统的影响下,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似乎文凭代表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和实际作为。教育部门很有效地利用了这种社会心理。党政官员领域的文凭风更是对此推波助澜。“知识化”是中国干部“四化”的重要内容(其它“三化”为“革命化”、“年轻化”和“专业化”)。不过,干部管理系统把此简单理解为“文凭化”。本科文凭已经大大不够了,好像一个干部没有一个硕士文凭或者博士就不可以成为好干部。于是,干部中间的文凭风盛行起来,导致了无数的假文凭的出现。
教育所能扮演的角色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但应当搞清楚的是,人们应当接受相关和正当的教育。对高教系统来说,教育必须要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在脱节的情况下,很难培养有用的人才。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脱节,教育已经严重阻碍着中国工业的产业升级。中国尽管早已经成为世界的制造工厂,但大量的产业工人数十年不变,都是农民工而非先进国家的技术工人。尽管中国一直强调技术引进,自己也有很多技术创新,但不能转化成为生产力,因为工人技术水平很差。同样一种技术由中国工人生产和德国、日本工人生产,附加值相差很多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尽管有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中产阶级规模得不到成长。原因很简单。技术类型的产业工人是中产阶级,而农民工不是。
在另一端,也是因为高教和社会经济发展脱节,高教教员生产出大量但处于知识链条底端的知识(论文),正如农民工大规模生产着低附加值的工业产品,教授、学者数量急剧增加,他们的产量也在增加。但是,高教系统所重视的只是一个数量,而非质量。搞“科研”就像搞群众运动,科研资源极其分散,不能有效集中,也不能有效吸引人才。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的人才培养演变成为实际层面的人才的“低质量化”。
在政治层面也是这样。教育对政府当然很重要,尤其对文职官员来说。但是,如果强调过分,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甚至是致命的结果。中国有很多历史经验,长达数千年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产生真正有才能的人才。科举制度产生了一大批只会考试而没有实际工作能力的“人才”。在封闭的情况,这些人才还有能力帮助朝廷统治社会。到了近代,一旦开放,他们就无能为力。这是科举制度解体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现在科举制度又变相地回来了,即公务员考试,考的内容往往是一大堆虚的东西,很少有技术含量。有很多学者论证中国为什么没有发生工业革命,为什么没有能力开近代化的先例?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虚空的儒家学说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忽视科学技术知识。现在,公务员考试越来越强调政治性,也有回归传统的意味。
实际上,政府内部的“文凭病”甚至可以导致政权的解体。这里,国民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当然不是说,教育没有用处。很多受过高等教育者具有容易和社会脱节的天然趋向,往往活在自己的“想当然”世界里,脱离社会,不知道社会实际上如何运作。他们往往从“社会应当如何”出发,很多改革经常过分理想化。很显然,从受教育程度来看,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共产党能够打败了国民党?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民进党能够打败了国民党?有人说,这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博士病”。有太多的人持有博士,这个政权就不会牢靠。
这并不是说,具有博士学位的人就没有能力,而只是说必须具有制度机制来连接教育和实际政治世界。
在考虑中国的教育往何处走的时候,人们不得不总结以往的经验和国际经验。教育改革必须培养有用的人才,而非空洞的政治家。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高教改革如果再继续在原来的道路上滑行,前面可能是死胡同。教育改革可能要“复辟”,要回归到改革以前的体制,即重视技术教育。很多三本甚至二本的大学(编按:收录高中考试成绩排后的第二批本科及第三批本科的院校)应当重新回归成为学院和技术学校。如果不能建立起一大批技术和技能学校,学无所用的现象还会继续下去。高教系统所培养的学无所用的人才越多,产业升级就越困难,政府治理能力就越差,社会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就越高。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