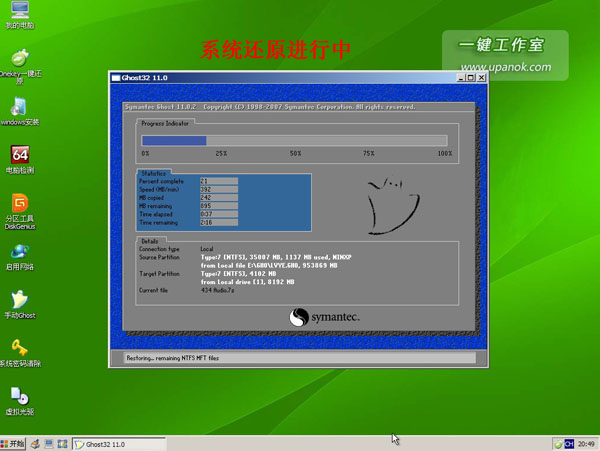毛泽东一生,诗词存世并非汗牛充栋,不过寥寥数十首、薄薄一册,不消一个时辰便可通览一过。然而,却可以从中窥探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可以全方位地了解毛泽东。其诗言志,未有雕琢隐藏处,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了解毛泽东的一把难得的钥匙。
偏于豪放,不废婉约
从现存的毛泽东诗词来看,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早年及中年时期;晚年时期。
早年及中年时期,毛泽东的诗词大多抒发激情,色彩和层次都很丰富,不仅有很多绮思丽句,其诗词意境也多具象。这些特点与早年及中年毛泽东的地位有关。到了晚年,毛泽东大权在握,雄视天下,身居亿万人之上,“四个伟大”加身,其诗词大多以咏志言志为主,哲理、典故在诗词中多有运用,意境大都抽象。
早年间有一些儿女情长的佳作,如写于1921年的《虞美人·枕上》,词云: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再如写于1923年的《贺新郎·别友》,词云: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翻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环宇。重比翼,和云翥。
这样的儿女情长,在毛泽东晚年的诗词中已难得一见。这种风格上的变化,与毛泽东的生活密切相关,也可以看出咏志和言情之间的差别。毛泽东曾经这样表露自己对诗词的兴趣,说:“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但是,其诗词中豪放者居多,而婉约者极少,及至晚年,则婉约几乎不见,更多的是豪放。像上述那两首赠予妻子杨开慧的词,少年时的儿女情长、愁思怨曲表露无遗,显示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拥有的七情六欲,而到了晚年,“伟大领袖、伟大导师”的光环已经将毛泽东神化,只剩下“不须放屁”这样的豪放、粗鄙之语。当播音员气宇轩昂的声音字正腔圆地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传进亿万中国人的耳朵时,这种“试看天地翻覆”的词句也让人们感到,这只能出自傲视一切的毛泽东之手。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其诗词都是气有余而韵不足,晚年尤甚。气韵兼备者,莫过于他的两首“沁园春”:早年的《长沙》(1925)和中年的《雪》(1936)。
长沙词云: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雪词云: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汉,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前者少年意气,挥洒自如,气韵皆备;而后者虽纵横捭阖,大开大合,王者之气显露无遗,已现欺韵之势。这样的情况,年愈长,则愈甚,大多数的晚年作品已经纯以气胜,艺术价值大大减低。
言志言事,以诗写史
纵览毛泽东的诗词,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可以通过这些诗词把毛泽东的一生串连起来,仅凭这些诗词就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生的大致轮廓。
毛泽东主张“诗言志”,这与中国传统诗学的主张相吻合。用诗词的形式言志记事,是毛泽东诗词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如他在1965年致陈毅的信中所说:“要做今诗,则要用形象思维方法,反映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古典绝不能要。”
毛泽东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也是斗争的一生,跌宕起伏,纵横捭阖。而他所经历的重大事件,在他的诗词中都能找到记录。从1927年的《西江月·秋收起义》到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从1927年的《西江月·井冈山》到1966年的《七律·有所思》,通读这些诗词,一部中共革命历史赫然在目,它们不仅记录了毛泽东自己一生的心路历程,也记录了中共走过的那些艰难曲折的道路。其记录的脉络完整而清晰,古往今来,似乎还没有哪位诗人词人能够如此完整地记录一个大的时代。
在言志记事的视野上,毛泽东的诗词大多采宏观角度,而绝少微观,没有明显的聚焦点,宛若摄影中的广角镜头;绝大多数的诗词,其视野都是远景。“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菩萨蛮·黄鹤楼》1927)、“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七律·长征》1935)等句都是这种视野的反映。而这种视野恰恰是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所特有的,所谓“小小寰球”,世界尽在其眼底。
在视角上,毛泽东诗词多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或鸟瞰,“背负青天朝下看”(《念奴娇·鸟儿问答》1965)是其习惯视角,这与毛泽东傲视群雄、睥睨天下的内在气质相吻合。毛泽东曾经说过:“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句话,在他的诗词中也有体现,这就是间或出现的视角的转变,或“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清平乐·六盘山》1935)”式的由仰视转平视,或“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七律·冬云》1962)”式的由仰视而转俯视。但在总体上看,毛泽东诗词还是以俯视的视角为主,这也与其“领袖”、“导师”的人君地位极其吻合。
在毛泽东的政治理念中,群众路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从国共内战时期的“人民战争论”,到中共建政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段。这一手段的极致,便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革,把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虽则说人民群众是毛泽东赖以依靠的力量,但是,人民群众兴风作浪背后的那只翻云覆雨手,恰恰是这位不怕死几百万人以实现个人理想的“人民领袖”,而人民群众不过是他巩固地位、夺取政权、清除异己的工具。诗言志,诗如其人,毛泽东诗词所采的视野和视角正是以人民为工具、以人民为群氓的一种佐证。
不拘一格,挥洒自如
1959年,毛泽东在致胡乔木的信中这样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1965年,陈毅请求毛泽东帮助改诗,毛在复信中说:“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因律诗要讲究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我看你于此道,同我一样,还未入门。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如同你会写自由诗一样,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懂一点。”
纵观毛泽东诗词,可以看出上述所言非虚。从严格意义上讲,毛泽东更多的是一个词人而非诗人。有论者云:长短句是毛泽东革命浪漫主义的标志。此言甚是。
毛泽东是一个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思想家,因为其大,故其诗词的立意多在放而不在收。早年诗词尚有约束,尚未达到从心所欲的地步,这一时期长短句多而律诗少,盖因律诗之讲究平仄、对仗,远远不能满足他抒发胸怀、表达壮志的内心需求。毛的律诗,大多出自1950年代,因为此时的毛泽东正处于其政治生涯的一个低谷,律诗要求之严格,这好符合他劲气内敛、韬光养晦的要求。但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他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齐天大圣,不拘一格、挥洒自如才是他真正期望达到的境界,于是,当他在政治上重新得势之后,长短句又开始增多,而早年的约束到了晚年已经荡然无存,诗词纯以气胜,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甚至连“不须放屁”这样的粗鄙之句都信手拈来,为其所用。此一境界,褒贬不一,但是其中所体现的境界却令人难以望其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