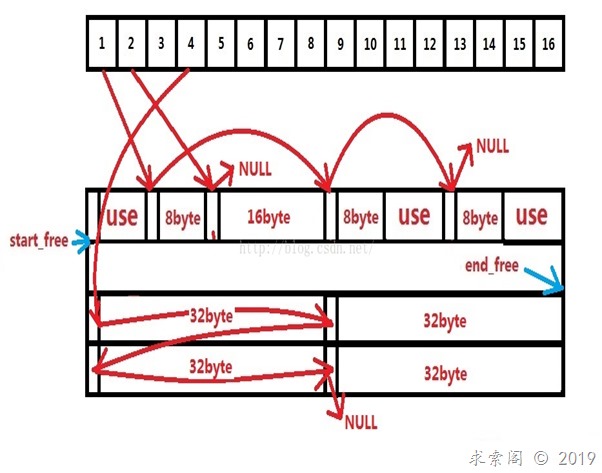阿拉伯世界发生“茉莉花革命”,在导致社会政治失序的同时,也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几乎陷于瘫痪。不过,很显然,社会失序并非新秩序的建立。尽管旧秩序已经倒塌或者摇摇欲坠,但人们不知道新秩序是怎样的?如何建立这样一个新秩序?这个新秩序和旧秩序又是什么样的关系?那种普遍认为革命之后就会是民主(化)的观点显然过于简单。
正如此前数次“颜色革命”,这次“茉莉花革命”虽然也不可避免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不过影响非常有限。尽管从表面上看,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中国毕竟不是阿拉伯世界。无论中外,那种认为那些迄今为止的非民主政权,迟早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颜色革命的观点,并没有多少经验上的根据。用“民主”和“非民主”或者“民主政体”和“权威政体”,来区分今天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并不确切。
从很大程度上说,在当今世界,所有政治秩序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不用说发展中国家,就连被美籍日本学者福山曾经视为是“历史的终结”的发达民主国家的民主秩序,也在受严峻的挑战。这些民主国家从前通过福利社会等因素造就了社会稳定,但当福利不可持续的时候,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产生了。同时,民主国家的政治秩序也经常因为不能产生一个有效的、比较强的政府而面临挑战。一些观察家也意识到,颜色革命也有可能发生在这些民主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政治问题更多,人们可以轻易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国家观察到。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较之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政治秩序制度化程度比较高,因而其吸收消化社会不稳定的能力也比较高。
中国并非阿拉伯世界
人们经常把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同时归属为“非民主政体”或者“权威政体”。不过,从深层次看,中国的政治制度至少在以下两个关键的方面,和其他的政体区分开来。首先,尽管共产党还是唯一的执政党,但已经逐渐向一个开放的政党演变;就是说,中国正在向开放的一党制转变。如果西方的多党制是通过外部多元化来解决政治问题,那中国开放的一党制是通过内部多元化来解决政治问题。以此相应,西方是通过外部政治竞争来保持体制的开放性,而中国是通过内部竞争(党内民主)和吸纳外部力量来保持体制的开放性。而无论是外部开放性还是内部的开放性,在阿拉伯世界是不存在的。
第二,中国各级领导层的更替制度已经相当制度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行以年龄界限为严格标准的退休制度、领导人任期制度,确立了新老领导班子的交替问题。这个制度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或者在后强人政治时代)得到了巩固。这使得各级领导班子的更新非常具有周期性和可预期性。实际上,这种制度和西方各类定期选举的功能类似,只不过是西方表现为外部竞争,而中国表现在内部竞争。这个制度更使得中国和阿拉伯世界区分开来。在阿拉伯世界,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个人专制制度。当一个领导人在位数十年而不变的时候,必然发生形形色色的腐败和专制。中国的政治制度当然还有待改革和改进,但从制度构架上看,中国的确建立了有别于西方民主和其他权威主义政体的政治制度。从领导层更替的速度来看,中国的制度远比很多民主政体更快、更有效。
和阿拉伯世界国家相比较,就社会稳定来说,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表现在社会秩序建设方面。很多层面的社会发展表明,中国社会矛盾可以随时激化,各种矛盾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不同民族之间,甚至不同精英群体之间。各个社会群体互相不信任,互相抱怨、仇视是正常现象,而相互合作和理解是例外。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民众的怨气越来越甚,小事易化大,非政治性的事件容易演变成政治性事件。例如,瓮安事件和石首事件均是由普通事件而引发的大规模的官民冲突,而新疆和西藏所发生的更是具有极强的政治性。
中国的社会秩序出现了什么问题?很简单,就是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之间的严重失衡。从经济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的成就是通过把经济过程开放给社会各个群体而取得的。但是近年来,经济过程变得越来越封闭,从早期的包容式发展转变成为排他式发展。既得利益倾向于垄断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都流向了少数人,大多数人很难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利益。这使得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严重,基本社会正义严重缺失。
从政治上看,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就是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并在国家的经济领域开始扮演重要作用。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尽管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但其必然具有政治性。如何面对新兴社会力量?这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在1990年代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那就是执政党承认这个变化,在此基础之上调整政治制度。当时,由于民营企业的崛起,国家便修改宪法和法律,保障私有财产。同时,针对民营企业家这个新兴社会群体,执政党实行开放政策,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一制度上的调整,大幅度地扩大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此后,这方面的进步就不是很大。针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利益,执政者不仅没有再进一步开放政治过程,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反而实行强化政治控制的做法,把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这尤其表现在所谓的“维稳”机制建设上。“维稳”机制如果是为了维持社会稳定,那么是可以理解的。任何社会都需要社会秩序,而社会秩序是需要机制来维持的。但如果“维稳”仅仅表现在通过强制性政策或者暴力,来控制已经崛起了的社会力量,那么就会适得其反,越“维”越“不稳”。今天的中国就是这样一种格局。
保持开放性与包容性
近日,中共领导层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这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就是要建设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社会秩序是继续1990年代的路径,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开放来吸纳更多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就会是里程碑式的政治进步。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开放,就会满足新兴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要求。同时,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会造就巨大的动力,促成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只有维持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中国的各方面的发展才会保持包容性,而避免排他性和封闭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性可以促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和约束。如何约束政府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在多党制国家,通过反对党制度来约束执政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制度,而各级政府又很难做到自我约束,那么就必须建立机制,让社会来约束政府。
前些年,中国领导层提出“不折腾”的口号,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因为人民需要生活,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实际上,“不折腾”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对政府提出的一贯要求。中国社会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不喜欢被“扰”,被“折腾”。历代皇朝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诸如“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等等政策,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可惜的是,这些年来,各级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对人民的“折腾”。对他们来说,“不折腾”只意味着社会、人民不要找政府的麻烦。这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拆迁。有官员甚至要“拆出一个新中国”来。全国各地,到处搞拆迁。一些老百姓好不容易修了房,想过安稳的日子,政府官员就过来要拆掉房子。用暴力手段“折腾”人民已经成为地方官员的习惯。例如医院和住房。任何人都需要居住所,也有需要看病的时候,但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地从医院和房地产获得暴利,使得老百姓看不起病,买不起房子。想一想,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民怨,哪一项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没有关联?
更为严重的是,对各级政府官员来说,“不折腾”已经成为“不改革”的代名词或者辩辞。健全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党政官员只对建设经济秩序有兴趣,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秩序建设,甚至用经济秩序取代社会秩序,结果演变成为人们所看到的兴盛不衰的GDP主义。不难理解,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都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社会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全盘的考虑,制度性的公民权的获得必须自上而下。在过去的二十多年,国家向社会收了那么多钱(税收),但有多少用于社会?中国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说法,很有道理。只有“用之于民”,那么当政府“取之于民”的时候,社会才自愿接受。但是当“取之于民、用之于己”的时候,社会必然抵制和反抗;社会和国家、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矛盾必然加深。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其社会不稳定都是因为政府不能或者无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所致。
很显然,中国的社会秩序建设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第一是要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成长。所谓社会秩序首先必须有社会。给社会空间,让社会成长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秩序,无论怎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都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最强大的国家力量或者行政力量,都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的。
第二是要进行意在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正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建设。所谓的公民权都是国家层面的,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无论怎样的地方建设都难以达致公民权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必须负有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
第三是要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没有社会参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所操纵,演变成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没有社会的参与,也很难构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内部的腐败变得不可避免。就是说,只有自上而下的制度建设,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的结合,才能保证政治的开放性、社会中坚力量的形成,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才是社会稳定的制度保障。诚然,任何社会都会存在一些对现存政府不满的因素,但只要这样一个开放的政治过程的存在,社会秩序就会是可持续的。
作者郑永年为新加坡国大东亚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