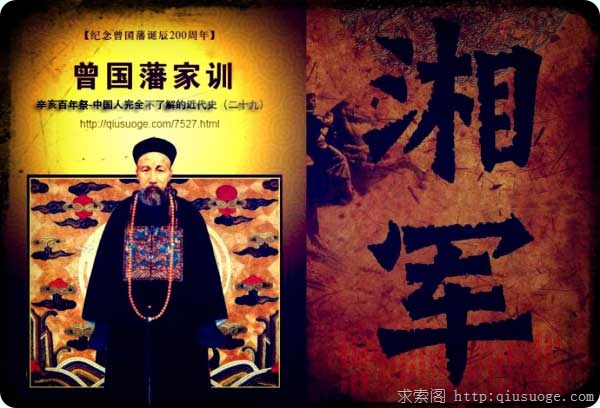群众路线在中国共产党所主导的政治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尽管历届中共领导层一直在强调,但这个概念及其所关联的政策,多年来也一直饱受党内外质疑。群众路线一直被毛泽东时期频繁发生的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似乎群众路线就是群众运动。如果是这样,群众路线应当被放弃。再者,那些强调制度建设的人,更认为群众路线与制度建设背道而驰,因此也应当放弃。
在毛泽东时代,群众路线主要体现为群众运动。每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群众运动必然会达到顶点。毛泽东也曾经探讨能否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即七八年来一次。毛泽东时代的经验说明,很难把群众运动制度化,因为运动本身是破坏制度化的;并且,每一次运动都会造成巨大的社会震荡和损失。但这既不表明群众路线可以放弃,或中共已经找到了其他更好的方式。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政府官员对人民的任意欺压。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并且越来越严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替代了“阶级斗争”,因为社会难以承受不间断的群众运动,阶级斗争产生不了执政党所需要的政治合法性资源。不过,在经济建设过程中,群众路线在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了,结果造成了执政党越来越官僚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官员的高度等级化。共产党无疑是世界上最具等级的政党。等级森严是执政党最大的特点。在党内,上级对待下级如同皇帝对待奴才,下级见到上级如同奴才见到皇上,上级脱离下级,干部脱离普通党员。所有政治组织包括政党,都有这种等级化的趋向。这也是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Robert Michels)所探讨的论题。但中国的情况更甚。中共是一个巨大的组织,需要高度组织化才能实现有效管理和运作。从横向看,党组织从其内核到外围,不知道存在着多少圈层。从纵向看,如同其政府,党组织本身也分为不同的行政层次,有效地把党的高层和基层隔离开来。
第二、政党行政化。近代以来,任何国家政治生活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政治和行政的分野。中国的传统政治也强调分野,王权就是政治权力,相权就是行政权力。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搞清楚执政党是政治组织还是行政组织。这制约了群众路线。在处理和社会群体的关系时,要不高度政治化,没有专业精神;要不高度官僚化,不讲政治。政治是要处理执政党和社会群体的关系,行政主要是执行执政党的政策。一旦执政党演变成为官僚组织,它和社会群体的关系必然产生严重的问题。
第三、最为严重的结果是,执政党与社会严重脱节。中共拥有8000多万党员,是群众性政党,但脱离社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今天的中国社会如此仇官,就是执政党和社会的脱节。群众路线就是官员走向社会,这是一条单行道,因为群众很难走向官员。一旦脱节,社会没有合理合法的途径影响官员,其诉求难以得到满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脱节,执政党及其官员就会失去执政的方向感和使命感,专注于个人、家庭和小圈子的利益,必然走向腐败。在这样的情况下,“天怒人怨”不可避免。
新一届中共领导层发动了声势浩大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和反腐败运动,尽管取得了成就,仍然面临艰巨任务,最主要的挑战是如何避免执政党的官僚化和去政治化。民主社会的政党也是如此,正如米歇尔所说,“寡头政治”是政党生活的“铁律”。但“铁律”并非“宿命”。要生存和发展,任何政党都必须找到抵制和克服“铁律”的有效方法。对中共来说,就是群众路线。
西方政治中也有群众路线,表述在民主政治实践之中。在多党制国家,民主政治通过周期化的政治动员,来克服政党的官僚化。每隔几年的选举就是一次政治化的过程。选举是制度化(即法治化)的政治动员运动。西方其他一些政治活动形式例如协商民主,也体现了群众路线。不过,民主在理论上和制度上的成熟,并不表明民主是最好的群众路线。相反,西方的民主越来越表象化,即政党的轮流执政和政权的和平转移,但它越来越不能为老百姓提供有效的服务,因为民主越来越表现为政党之间的互相否决,政府弱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在亚洲,民主或者多党制度,更是面临着过度政治化的威胁,民主政治主导一切,政治人物互相否决,行政被弱化,政府被弱化,经济社会出现很多问题,不能有效治理社会,甚至出现治理危机。
中国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毛泽东说过要用民主的方式来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就是前面所说的每隔几年来一次的群众运动。但这已经被证明很难持续。不过,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执政党今天仍然面临官僚化的最大威胁。
群众路线要成为中共生存和发展的有效方法,必须既表现为理论,也表现为制度。在中国,群众路线仍然停留在偶尔发生的(非制度化的)政治实践上。这也就是一些人总是把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等同起来,因为在没有理论和制度的情况下,群众路线是否存在,就取决于领导人的个人偏好。
首先必须解决理论上的问题。群众路线被边缘化,首先是因为人们在理论上对此很模糊。近年来,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流行着很多驱使执政党“非政治化”的概念。例如“执政党的自主性”概念,就是说执政党不应当受任何社会力量的制约,在政策制订和实施过程中具有高度自主性。这是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界所提倡的“政府(国家)自主性”的中国翻版。在西方,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西方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他那个时代)。但后来人们发现,其实政府拥有高度的自主性,在决策和政策实施时,不代表哪个阶级或利益群体的利益。不过,把这个概念机械地使用到中共,就非常危险。如果“自主性”意味着执政党在决策和执行政策时,不能被任何既得利益所绑架,这可以理解;但如果意味着执政党可以脱离社会而自主决策,则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另一个观念就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非常流行的“行政吸纳政治”。这个概念主要用于解释香港、新加坡等地的行政经验,因为政府能够提供充分的社会服务,就不需通过西方那样的政治了。这实在是误解。香港在港英时期不需要政治,因为香港的政治由伦敦说了算,香港人毫无权利去谈论、参与政治,香港的公务系统只是执行英国人的政治意志。在新加坡,尽管行政效率非常高,但其背后就是政治。李光耀之所以能够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是因为他是最讲政治的。只不过是新加坡的政治主要表现为制度和专业主义。新加坡的很多组织形式,都有当时共产党组织的影子,只不过表现为法治形式。因此,群众路线在新加坡高度制度化,部长和议员每周定期要接见和解决选民所面临的问题。在民主政治下,只有到了选举的时候,政治人物为了选票,才开始和社会接触。但新加坡的执政党和群众的互动是每时每刻的。当然,加坡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行政效率最高,也不能吸纳政治;相反,高效率的行政,必须基于有效的政治之上。
同样重要的是群众路线的制度体现。这更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国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首先是群众路线必须在制度上体现党的性质。中共是中国政治的核心,党管政治,因此党应当是联系群众的工具,必须是群众中间先进的部分,否则执政党的合法性就会成为大问题。如果说民主社会,政治官员的合法性是民众的投票“投”出来的,中国政治官员的合法性,应当是走群众路线“走”出来的。这方面,中共在录用政治官员时,需要考虑到群众自下而上的评估(而非仅是党内的评估),并且需要制度化。1980年代提出干部“四化”,即革命、年轻、知识和专业化。从制度层面来说,后三项比较容易量化,实践上也得到了强调,但第一项最重要的却被忽视。当然,在建设年代,对“革命化”应当做不一样的解释,主要是干部要懂政治,也就是群众路线,深刻理解他们的权力来自群众,要向群众负责。政治官员没有专业化和知识化不行,但不讲政治也不行。
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是政治和行政的相对分离。政治强调路线方向,讲人民的满意和国家的长远利益,而行政强调政策执行,讲效率。在行政方面,专业主义非常重要。这一块,现在仍然存在着政治化过度的现象,需要减少政治化的程度。司法、教育、文化等等领域的政治性仍然过度,而专业主义不够。但在政治领域(主要是党务领域),则应当要更多的扁平化。不仅要在党的高层和基层之间,也要在党的高层和普通群众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表现在组织构架上,就需要把政治系统和行政系统区分开来;表现在人事制度上,应当把培养政治人才和官僚人才(公务员)的制度区分开来。目前用培养官僚的办法来培养党的官员,很难培养出好的干部来。
在政策层面,群众路线要求政策研究和决策的相对分离。现在,政策研究和决策部门几乎是同一批人。党的政策研究必须走向社会,研究者不需要任何行政或党内的级别。一旦具有了级别,就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情况。走出衙门,研究者都被社会视为官员(他们实际上就是官员),没有人会给他们讲真话;同时,高级别的官员也很难接触到基层群众。
在政党内部,也需要实现精英化和群众化之间的平衡。在和平执政时期,政党的精英化不可避免,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先锋队”的角色,但群众化也不可被忽视。对中共来说,问题是如何使用好庞大的党员队伍,尤其在基层。这里可能就要区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在新加坡,干部党员(也就是精英)一般都是在政府担任政治要职,而基层党员或者普通党员,就是执政党和社会的关联点,两者配合和结合得非常好。中国这方面仍然有很多改善的空间,尤其是对普通党员的使用上。在现行体制下,大量的普通党员是被边缘化的,没有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执政党的开放,向普通党员和社会群体的开放。开放是任何执政党避免既得利益化的唯一选择。一旦既得利益化,政党必然形成寡头政治,走向衰败。人们经常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来形容中共,这非常恰当。这里的“营盘”指的是作为组织的中共,而“兵”指的是党的干部党员。如果执政党不想被任何既得利益所垄断,开放便是最有效的办法。
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更多精彩,尽在–
| 1、乔良文集 | 2、占豪文集 |
| 3、郑永年文集 | 4、井底望天专栏 |
| 5、活学三十六计 | 6、毛泽东传 |
| 7、上合贴 | 8、刘涛-中国崛起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