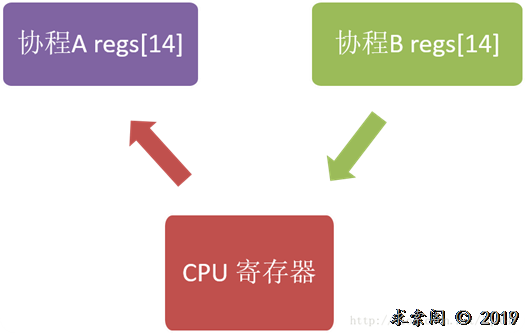——读司马光《资治通鉴》随想
【内容提要】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而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又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研究表明,公元一千年前后,欧洲经济处于最低点,而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其哲学成就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空议之风大盛,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为了“补天”,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 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关键词】资治通鉴;实事求是;学风;国运
说明:本文是为拙著《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二版所作的序言,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一期。原题为《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
我在2010年底出版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一书中卷的自序中,曾说我写前两卷即上、中两卷是在为中国未来经营和治理世界提前做的“资治通鉴”准备[1]。这里我想就《资治通鉴》再多说两句,因为它关乎学风,而学风则关乎国运。
《资治通鉴》出现于北宋(公元960?1127)不是偶然的。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表明“西欧收入在公元1000年左右处于最低点。其水平显著低于其在公元1世纪时的水平,也低于同期的中国、印度以及东亚、西亚的其他地区的水平”;麦迪森同时也认为“11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2]。这就是说,中国宋朝经济已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巅峰,同时也处于世界历史政治转换即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新起点。司马光(公元1019?1086)和他的《资治通鉴》就诞生在这个世界文明新旧转换,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3]的节点上。
遗憾的是,在这个节点上,代表新文明方向的并不是司马光,而是比他晚出生128年的意大利学者但丁[4]。恩格斯评价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5]同是站在历史大转折的节点上,但丁在开辟着世界的未来,司马光则在挽回世界的过去。尽管如此,司马光还是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黑格尔的作用相似,黑格尔用维护德皇国家体制的保守形式,在形而上学笼罩的欧洲意识形态中,为即将来临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保存了辩证法的思想火种,它最终催生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他们的学说为世界文明迎来了社会主义前途。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本意在于“补天”,但其中那字字血、声声泪的内容体现出的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则挽救了整个中华民族。
国家多崛起于贫寒,衰败于恬嬉。宋朝世风侈靡,国富而兵骄,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还主要是它那脱离实际的浮华学风。
宋代哲学成就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此同时,人的认识离实际却是渐行渐远,唯心主义成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北宋(960?1127)末期周敦颐(1017~1073)及其学生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将“太极”之说推高至普世“天理”,认为理先于事,“天下只有一理”[6]。这时的“理”,类似今天一些人讲的所谓高于具体国情的“普世价值”。这导致宋代政学两界空论风盛:为事者“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7],为政者则“好同而恶异,疾成而喜败”[8]。人取仕途功名的路径与实际经验严重脱节,这使国家许多官员的政治见识多流于“纸上空谈耳”[9]。苏辙(1039?1112)曾向皇帝痛陈:“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为士者日多,然而天下益以不治。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仰不养父母,俯不恤妻子,浮游四方,侵扰州县,造作诽谤者,农工商贾不与也。祖宗之世,士之多少,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然其削平僭乱,创制立法,功业卓然见于后世,今世之士,不敢望其万一也。”[10]这种现实与盛唐时那“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11]的情势形成鲜明反差,而与目前中国大学生蜂拥直考国家公务员的情势及其后果却十分相似。
人的思想及其理论一旦脱离实际,学风也就随之堕落,接踵而至的就是国家的衰落。与苏辙同代的司马光也感受到空谈普世价值(即所谓“天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他虽身系朝政,却仍无力回天,无奈只有将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寄托于笔下。在司马光笔下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民生休戚”的历史事件,其目的是“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12]全书因事命篇,直面矛盾,以周天子导致国家分裂、诸候雄起的政策失误开篇[13],记载了长达1362年的历史,一个故事一滩血,没有口号,绝无大话,更无空话。它犹如暗夜里闪电,晴空中惊雷,与当时那严重脱离实际、空论普世理学的学风[14]形成强烈的对比。尽管《资治通鉴》没有警醒沉缅于诗词书画中的宋代朝政,甚至没有警醒做秀成瘾的明代朝政,但它警醒并挽救了中华民族。明亡后,中国大凡有作为的政治家,案头首选多为《资治通鉴》[15]。其中那经世致用、不尚空谈、实事求是的学风,为后来中国那“一天等于二十年”[16]的迅猛崛起奠定了认识论基础。
有生命力的思想崛起往往是以物质社会的衰败为代价的。《资治通鉴》在北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认识大转折的萌动。宋、明这两个富得流油的王朝为北方强势崛起的马上民族所倾覆,这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刺激,以至南宋的“普世价值”(天理)大师朱熹(1130?1200)也强力主张将《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这几部重视实际经验的著作并作“四书”,作为国家教育和科举的至尊课目。
与历史上许多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改革在完成它的使命后便遭遇“否定之否定”命运一样, “四书”被列入国家科举的主修课目的教育改革,在其初期——尽管它后来也走到自身的反面——对当时的中国思想进步还是产生了重大的积极意义。《大学》将“正心”作为人生事业即“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绝对前提,其意义在于要求知识分子在改造客观世界之前先改造主观世界,要求治学应先有明确而坚决的立场,而不能有那种“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17]式的相对或说无“诚意”的立场。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论。此外,《大学》强调“格物致知”,这是东汉学者班固(32?92)——大概是对西汉(公元前206?公元后23)大衰败反思的结果——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经北宋普世“理学”的否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得到肯定(恢复)。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1472?1529)将《大学》中的这些思想概括为“大学问”[18],以与以前那种“不事其本,而先举其末”的小学问相区别。与宋末比较,明末清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学风已发生了大变化:王阳明及随后的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乃至清末曾国藩(1811-1872)、左宗棠(1812-1885)等,都不再象宋朝的知识分子那样文武分离,而是主张知行合一,身体力行。他们不仅学问好,而且习武,有的还领兵打仗。《资治通鉴》以及“四书”中展现的重经验、轻先验、经世致用、不务空论的认识方法,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民族危机的历史关头,成了中国政治思维的主线。20世纪40年代,这种认识方法又经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的继承性改造[19],形成了以“实事求是”为精髓[20]的“延安学风”。这种学风有力促成了20世纪中国——不仅是中国,英国、美国崛起时也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杜威的实用主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崛起。
生死之地见真理。回头来看,当年毛泽东和王明开展的那场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争论及其实践检验结果,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仍是一份极为珍贵并值得我们在未来历史中不断体会的思想遗产。而这次思想转折发生的起点,恰恰就是1934年底湘江之战的惨败。流血了,人就知道真理;面临生死,人就不空谈了。可以说,没有这次几乎是毁灭性的军事失败,全党就不会认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
17世纪初,莎士比亚将“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21]摆到已来到世界新文明门坎的英国人面前,英国人民用资产阶级政治革命和随后的工业革命,不仅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由此还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民在世界新文明即社会主义文明门坎前也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今天,中国开始从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向世界性的国家转变,在这个新征程中,“生存还是毁灭”的问题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再次摆在中国人面前并需要我们用新的方法去解决。
每当面临新的历史性难题,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想到毛泽东。20世纪40年代,周恩来同志曾向全党发出“学习毛泽东”的号召,他说:“毛主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化在中国土壤上,生长出来成为群众的力量,所以中国革命得到如此伟大的胜利。到今天,不仅中国共产党尊敬他,凡是得到革命胜利果实的人民,一定都会逐渐心悦诚服地信服他。”[22]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学习毛泽东”仍是摆在21世纪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的任务。新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多政治成熟的领导人和国家公民。政治成熟,意味着我们认识摆脱了“左”右两方面的“幼稚病”[23],诚如邓小平同志总结的那样:“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24]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同志及其战友们的经验中学到可用于当今的有益知识。
1972年有两件值得研究的小事。第一件是当年毛泽东对到访的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25],第二件是毛泽东要求到中央工作不久的王洪文阅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26]。毛泽东意在警示王洪文,政治问题并不是靠你登高一呼就可以解决的。你没有沙场历练,如果再不向老同志学习、多长进,结果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也会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如果将毛泽东两次谈话内容联系起来,可知毛泽东当时的忧心所在。随尼克松来访的基辛格巧妙道出了毛泽东的担忧,他说:“美国的左派只能夸夸其谈的事,右派却能做到。”[27]
基辛格说的问题,在当时既存在于美国和苏联,也存在于中国。王明的“左倾”空谈和赫鲁晓夫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巨大灾难[28],这让毛泽东在晚年对当时那些只知空喊的“左”派——这些人用斯大林的比喻就是“属于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或者像飞蛾投火的共青团员”[29]——的治国能力深感担忧,他担忧未来的中国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5月15日,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30]此前两个多月,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他要求“教育革命”,他希望在新的教育制度中学生不会脱离实际,不会“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31],其目的就是要防止远如大宋近如苏联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2]在研读宋明这段历史时,我常联想奥地利。奥地利在19世纪曾是雄视大半个欧洲的奥地利帝国(1804~1867)和奥匈帝国(1867~1918)的国都,其首相梅特涅在拿破仑失败后的维也纳会议上还是决定欧洲政治的关键人物。可它到20世纪却成了在地图上需要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袖珍小国。沧海桑田,往事并不如风。公元前403年,周天子威烈王正式分封韩、赵、魏为诸候,由此导致国家分裂,战国纷争。好在此种乱局于公元前221年为秦王嬴政定为一统,中国由此有了在亚洲迄今不能撼动的主体性大国地位。[33]
面对同样的事件,欧洲人就没有这么幸运。公元800年,查理大帝将群雄纷争的欧洲归于一统,其历史贡献类似中国的秦始皇,可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统一的欧洲就为查理大帝的三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孙子于843年竟用一纸“凡尔登条约”[34]一分为三,这不仅奠定了后来意、法、德三国的雏形,而且在欧洲大陆地缘政治中深埋了极难修复的破碎性的根基,这反过来为欧洲绵延千年之久的混战及为欧洲大陆边缘的不列颠岛国最终成长为世界大国提供了天然的地缘政治条件。20世纪日本人很重视英国利用欧洲地缘政治的破碎性操纵欧洲大陆的经验,并于40年代将中国分割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四分五裂的局面。有幸的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1949年实现了国家统一。
“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5]新的历史条件使中国人不得不考虑参与经营和治理世界的问题。而在这方面,与西方人相比,我们还处于相当没有经验的初学阶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是否严肃思考过20世纪初期奥地利和末期苏联所遭遇的厄运是否会在21世纪降落中国,以及为避免这种厄运,我们应当担当些什么责任。
这样的责任感迫使我考虑写一部总结西方人经营和治理世界经验教训的“通鉴”式的著作——这是我撰写三卷本的《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初衷;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将写作的主要精力用于显示什么“新思想”,而用于证明某种成熟有效的经验,尤其是大国博弈中因决策失误而留下的生死经验。
书生切莫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36]。显然,写这样的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式的热闹就能完成的。从2005年始至2010年底,我完成了本书的上、中两卷共150万字的写作和出版任务。在键盘的敲击声中,我仿佛听出当年司马光写作《资治通鉴》的弦中琴音,意识到我们与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也在担当着民族复兴的责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知识分子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希望所在。
现在我已着手准备本书第三卷的写作。需要说明的是,当我这部三卷本的著作最终完成的时候,读者便会从中看到一个近代以来世界大国力量分布及其互动的坐标系:上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国家和北美洲大陆国家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近现代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东西横向互动的坐标横轴;中卷研究的是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即俄罗斯和印度与其他大国之间的博弈能力的底线和极限,这勾勒出同期大国政治力量分布及其南北纵向互动的坐标纵轴。由此我们可在这个坐标系中进一步找出中国及其未来发展的坐标位置及其力量伸展的可为空间和不可为空间,而这正是我今后两年将要完成的写作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