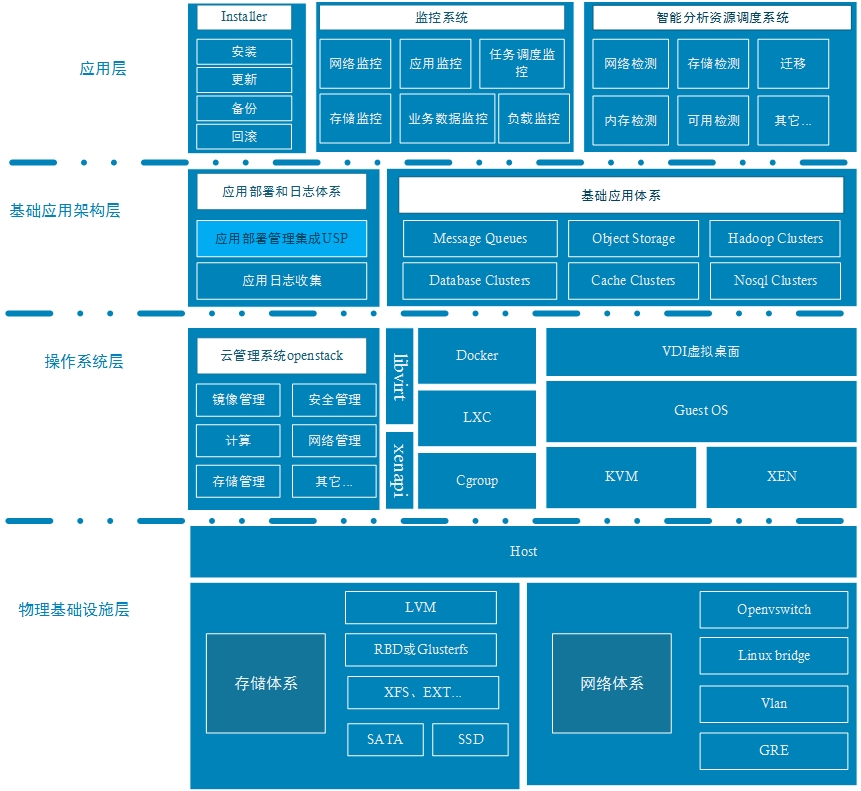讨论中国今天的教育哲学问题,避免不了中国传统教育哲学问题。中国传统的教育哲学是怎样的呢?讨论教育哲学不能过于抽象,而应当回答“谁的教育哲学?”这个问题。这里,我们首先应当关心的是教育者和知识界的教育哲学,因为这个群体是教育的主体。无论是知识传授还是知识创造,这个群体的教育哲学是决定性的。那么,传统上,谁是教育者呢?
中国道教与佛教的内部教育
传统道家有针对其弟子的教育哲学,但没有发展出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强调个人道德的发展,但没有社会教育哲学,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道家对社会少有关心。道家向往的是与世界隔离的生活,这个群体以山林树木为伴。这就决定了这个群体不可能发展出面向社会的教育哲学。道家因此是一种道地的人生或者宗教哲学。第二,道家也有方法论上的问题。道家关心自然世界,又坚持独立个性,不依附权力和利益,从这个角度上看,道家是最有可能发展出知识体系来的。但实际上则不然。为什么?除了不关心社会现实之外,主要是方法论上的问题。知识体系来自主体对客体的研究,但在道家那里,主客体是不分的。道教坚持人与自然的合一,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一思想具有非常的现代性,甚至是后现代性。但因为主客体不分,道家没有发展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尤其是和人类社会有关的知识体系。
和道教一样,佛教也有针对其信仰者的教育哲学,但没有针对社会的教育哲学。这和西方宗教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教育尤其是大学源自宗教,当然从宗教到大众教育,这是一个复杂和痛苦的过程。中国的宗教没有演变出大学来。这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来,并不是说这是中国宗教的错。宗教的对象是社会大众,但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来。从学术上看,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道教不关心社会,很容易理解。但佛教则是非常关心劳苦大众的,为什么也没有发展出教育哲学?这可能和佛教不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宗教有关。佛教强调“空”、“出世”等概念,满足于现实,着眼于“来世”,这使得其不关心现实和改造现实,这和西方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传统的儒家教育哲学
儒家教育哲学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第一,和关心自然世界的道家不同,儒家既不关心自然世界,也不关心外在世界,即“敬鬼神而远之”。儒家不否认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对此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形而上”哲学,和儒家的这一态度有关。当然,也正因为儒家的这一态度,中国文化演变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世俗文化。
第二,儒家关心的是人们生活于此的这个世界。不过,总体上说,儒家关心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造这个世界。或者说,儒家是一种规范哲学而非实证哲学,它所关心的是“世界应当如何?”而非“世界实际上如何?”的问题。
第三,儒家强调通过政治权力来改造世界,因此把知识和政治、学者和政治家领域紧密联系起来,即“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在儒家那里,成为对国家有用的士大夫,就是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使命。
第四,儒家的道德哲学消除了在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世界等领域的边界。儒家把道德视为是政治的根本,其核心就是“德治”。而“道德”寄存的基础是家。因此,儒家强调“国之本在家”。这样,把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和国家治理联系起来。“修身、养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家到国家,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边界。儒学经典《礼记·学记》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
着眼于现实政治世界,着眼于政治权力,着眼于人才教育,这些因素使得儒家成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发达的政治统治哲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阶层是最职业和专业化的。
儒学教育的问题
不过,同时儒家的教育哲学对中国教育和知识生产本身产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规范性教育哲学,而非实证性教育哲学。儒家过于强调“应当怎么样?”使得其在很多方面过于理想,不考虑其所提出的理念能否在现实世界实现。在儒家那里存在着一个非常深刻的内在矛盾,那就是,一方面有强烈的意愿改造社会,建设一个好社会,但另一方面因为仅仅从规范出发,对现实社会到底是怎样的没有深刻的认识,结果儒家改造社会的努力往往很成问题。在没有对现实世界作解释的情况下,又如何能够改造世界呢?儒家教育哲学没有发展出能够解释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知识体系来,哲学始终停留在规范层面,和现实社会并无多大的关联。尤其是当现实社会的发展不能吻合儒家的理想时,士大夫阶层不是随时修正自己,更多的是积极干预和阻碍社会变迁。儒家缺少社会进步观念,其自身的变迁往往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变迁。
第二,儒家的教育过程过“硬”。儒家强调教育没有错,但儒家的教育过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理论上人人可以成儒,但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儒。一个人的“儒化”的过程,也就是儒家的灌输过程,显得非常“硬”。这个过程远比在西方个人宗教化的过程要困难得多。西方的宗教是针对大众的,而儒家的对象是精英。西方人称儒家为“儒教”显然不是很精确,因为儒家充其量是精英宗教,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意在塑造政治精英的“宗教”。
第三,与之相关,儒家所提倡的“有教无类”那么先进的思想并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和西方相比,中国文化中并不强调民族、种族、宗教、阶级等等在西方决定一个人身份的因素,而是强调教育在塑造人的过程中的作用。在中国,社会成员只有“受教育”和“没有受教育”之分;进而,每一个人不仅有权利接受教育,并且也能被教育好。但为什么中国传统没有发展出类似西方的大众教育呢?这和儒家社会化过程的困难有关。西方从中国学到“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并很快孵化出大众教育的思想。西方的宗教是面向大众的,“有教无类”非常吻合西方的宗教精神。
第四,更为重要的是边界和专业主义问题。知识应当是没有边界的,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传统儒家教育哲学是有边界的,即着重于政治或者统治哲学,而忽视其他方面的研究和教育。另一方面,儒家教育哲学则没有确立知识的边界,尤其是和政治领域的边界。它强调学者对政治的参与,政治和学术之间没有建立起边界,经常导致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关系过紧。从知识体系确立和发展的历史看,知识的边界问题非常重要。知识的目的就是知识,就如资本的目的就是更多的资本、政治权力的目的就是政治权力一样。因为边界的缺失,儒家也没有发展出强烈的专业主义精神来。儒家知识分子的功利主义精神过于强烈,没有“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知识”的专业意识。
第五,缺失独立性。没有对知识的认同,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使得儒家缺少独立性。在没有自身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儒家主要想依靠君王来改造世界,这导致了对权力的过度依赖。没有独立性也就是不能形成知识分子的自治群体,这对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和其他领域的关系的影响很大。对王权而言,知识群体是个依附型群体。这个群体千方百计想为王权提供有用的知识,但实际上,所提供的知识实在很有限。很多场合,儒家所提供的仅仅是“统治术”。对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儒家往往把自己道德化,在很多场合演变成训斥人的哲学。儒家哲学里,社会是具有等级的,即士、农、工、商。儒家把自己放在首位,而这个“首位”主要是儒家认为本身掌握了社会所需要的道德。对社会而言,儒家也没有进步观。儒家主要着眼于根据现存的条件优化统治方法,这里面是没有进步观的。儒家强调统治者要根据现实而变化,但儒家里面是没有追求变化的因素的。因此,儒家也历来被视为是一种保守哲学。
儒家的保守性也影响了其和其他知识群体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的研究所展示的,中国历史上也有辉煌的科技成就,但是中国的科学实践知识没有演化成科学知识体系。更有意思的是,在其他社会,科学知识往往总是积累的过程,也就是一直往前走的,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科学知识的大突破,但中国的科学知识往往出现退化的现象,也就是往后走。实践知识不仅没有积累,往往被毁掉。为什么会这样?这里的因素很复杂,但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以儒家为核心的统治哲学。当儒家或者儒化的官员(士大夫阶层)看到一种技术或者技术知识会导致变化,影响其心目中的道德政治秩序的时候,他们必定和王权结合起来共同反对之。
儒法并用的统治哲学
上面讨论了作为知识群体的儒家的教育哲学。那么,社会上其他群体有没有教育哲学呢?中国的政治领域或者政治人物也有教育哲学。传统上,王权是有教育哲学的。这里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法家。法家往往是统治者。法家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知识,也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但和儒家比较,法家并没有申明自己的教育哲学。
不难理解,王权的教育哲学的核心就是维持其统治。皇帝在统治社会时往往是儒法并用,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软力量和硬力量并用。儒家可以说是软力量,而法家是硬力量。儒家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权的意识形态,是因为儒家接受了王权的改造。早期儒家,尤其是在孔孟时代,是非常独立的,这些儒家的先驱周游列国,推销自己的治国理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畏权势,具有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皇帝当然会不高兴,在儒家和王权之间经常呈现紧张关系。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是这种紧张的表现。后来为了适应王权的需要,儒家开始接受改造,把自己改造成为王权服务的知识体系。在改造过程中,儒家也强调讲真话,但因为儒家对王权的高度依赖,讲真话在理论上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讲真话的空间很小,甚至不可能。真话能不能讲,有没有用,主要取决于皇帝本人。在一些时候,例如宋朝,皇帝愿意和士大夫阶层分享权力。但在更多的时候,士大夫阶层讲真话甚至会招致杀身之祸。这一趋势一直延伸到毛泽东时代的“反右运动”。培养一个“听话”的士大夫阶层是王权教育哲学的核心。
中西方商人阶层的教育学
中国的商人也没有教育哲学。商人在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等级中处于最后一位,其没有也不被容许发展出其自己的教育哲学来。商人阶层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儒家所承担的。中国的王权发展出了很多方法来消解来自商人的挑战。首先是把商人放在社会等级的最底层。一旦商人致富,就会要求他们收买土地、官职等,以免商人积累过多的财富对王权构成威胁。同时,商人也被灌输于“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把接受儒家教育视为是其子女的唯一出路。可以说,中国商人在教育方面没有发挥一个重要作用,这和西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方,商人阶层在教育哲学方面扮演了一个关键作用,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促成了教育和神学的分离。西方在中世纪是神权时代,神学是知识体系的核心,当时所谓的教育就是神学教育,神学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但文艺复兴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文艺复兴之后理性主义兴起导致了神学时代的终结。“终结”当然不是说神学不存在了,而是说神学不再占据知识领域的主导地位。理性主义的兴起有其知识背景,但商人阶层的崛起极其关键。商人是最讲究理性的,商业行为不能用神学来解释。新兴商人阶层站在文艺复兴的背后,是文艺复兴的经济基础。第二,促成了知识和政府的分离。商人需要能够支撑商业运营的知识体系,尤其是法律。同时商人也担心政府的力量过大。知识和政治的分离对商人非常有利。知识界争取和政治权力的分离,商人是背后的推动和支持力量。在西方,大量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都是私立的,这完全是商人的功劳。没有商人的支持,西方难以发展出如此独立的知识体系及其生产知识体系的机构来。
政治、商业和知识三者之间的不同关系构成了中西方不同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知识领域没有独立性,成为政治权力的一部分。而政治的最高目标就是秩序,创造秩序和维持秩序。秩序就是保持现状,不但不追求变化,反而阻碍变化。在西方,知识界不仅独立,而且往往和商业结成联盟。和追求秩序的政治不同,商业所追求的就是永无止境的变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哈佛经济史学家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把资本主义定义为“创造性毁灭”的过程。创新和进步是商业的特征,正如秩序和稳定是政治的特征。而知识是关键,知识既可以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变化的一部分。到今天为止,中西方教育和知识界仍然维持着这种差异格局。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北京,2012年4月21日)上的发言的第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