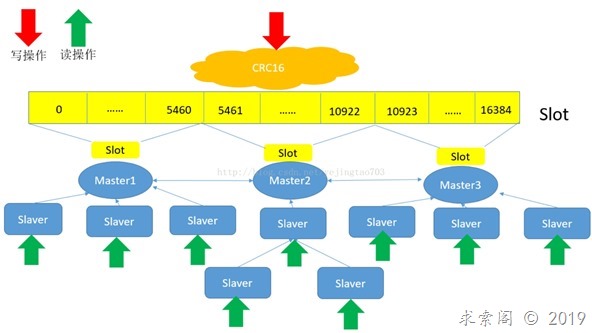上一章讲了不言之教,无为之益的道理。与之相反的呢,则是有言之教,有为之身。本句里的名,指有言,对应的是不言之教的反面。身,有为之体,对应的是无为之益的反面。
先有不言之教,后有无为之益。其反面,也是如此,先有名,有名之后,可言可说,进而,人以这些名教言说,构建成一个”自我“,这个自我,就是身。在道德经看来,人的自我,只是后天的一种发明,是知识的产物。
人本来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道德经认为,所谓返璞归真之人,无名无欲无身无为,能同于道未生无,无未生有,有未生万物之前的那种虚境,从而可知道之大,虚之通,这就是大通之境。
名,就如同积木一样,人用它们来搭建自己,组成了一个我,这个叫做我的事物,本来就是外部世界的素材,人用外部世界的素材,来搭建了一个和自己无关的我,这个自我之身,和那些构成这个自我之身的素材,都只是身外之身而已。
名是你呢,还是身是你呢。既然都不是你,那么又和你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没有关系,那又何亲之有呢。
身与货孰多?
以有名之身,行有为之事,天下之事,为而执之,无有穷尽。怎么做,也做不完,怎么追求,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人的一生,一旦落入了这个有名之身,他就坠入了有限之中。人即便有再大的能力和精力,即便生命也足够长,那也只是多点和少点的区别。本质上,也根本摆脱不了这种有限性。
货,就是人要去追逐的事物。事物总是在变幻,在时间纵深上没有止境,在多样性的广度上,也没有止境。人以有限之生命,在面对这么多无穷无尽的外部世界的对象时,显得是那么的无助。你来追我呀,怎么追,都比你多无穷倍。
得与亡孰病?
尽管是那么的眼花缭乱,还是去追了。就如同走进了一片欲望的森林,森林里什么都有,看到什么都想拿,都想拥有。可是,怎么也无法一次把所有的漂亮衣服都穿完,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吃完,得到一个,就意味着错过了其他的所有。这么看,得难道不是失吗。
既然注定不能得到所有,那么错失过的那些,就真的比手里现在得到的这个好吗?要不干脆,把所有的都失去呢,会不会心里没那么多遗憾呢。
以有名之身,行有为之事,既不可能得到全部,也不可能失去全部。在得失之间,不管进退,都是亏。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本来,域中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天地万物,还没有被生出来。接着,天地万物被生了出来,不同的事物之间,别有了差异和天性,于是要标划描述这些不同的事物,只能分门别类,这是这个,那是那个。
既然有了彼此,那么自然的就会有是非。有了是非呢,人就会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喜欢的呢,就想越多越好,不喜欢的呢,就希望越少越好。道生万物,万物初始为一。有了名相和是非呢,一就被裂为万。
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如果万物为一,何为此,何为彼,何为是,何为非?一裂为万,道之亏也。穿梭于万种碎裂细物的杂多乱亡之间,是其是,非其非,爱之所以成也。
爱之甚,必藏之多。藏之多,道必亏之尽。道亡,藏之愈厚,祸败愈烈。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
道之不亏,为全。一之不裂,为足。能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就不会役累于物,而是以道御物,使万物自来归附于自己。物为君,己为臣,物为上,既为下,此谓大辱,失道而不可御物。
明万物为一,又知万物之所名。既不亏道,对万物亦能应而不遣,观而不乱,静静的看着它们归附自己,而不动不燥,不欲不为,不厚不薄,以静笃而守之,是谓知止。知止,则道不亏,德不悖。道全德足,故可以长久。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名与身孰亲?
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
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