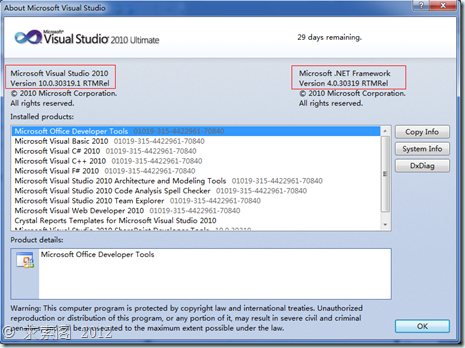今天我们常以“一生一世”来起誓,“一生”词意很明白,就是一辈子,但是你可知道,“一世”又是多少年?
世,《说文解字》中说:“三十年为一世。”一世并不代表一辈子,而只是三十年。金文的世,是止字上面加三点,即表三十年。《论语·子路》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孔子是说,如果有君王兴起治理国家,也必须要治理三十年,然后才能实现仁政。《宋史·张咏传》就记载了一则关于“一世”的有趣故事。张咏和傅霖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张咏做了大官,傅霖却隐居不仕。30年后,傅霖才来拜访早已显贵的张咏。门房向张咏通报有一个叫傅霖的人来访,张咏呵斥道:“傅先生乃天下贤士,你竟敢直呼其名!”傅霖听后,大笑着对张咏说:“别子一世尚尔耶?是岂知世间有傅霖者乎?”就是说,我和你分别了“一世”三十年,世间哪里还有知道我傅霖名字的人呢!
我们现在常用“世界”一词来指代很大的范围,甚至是全部、所有、一切。然而,从世、界两个字来看,世字本义是三十年,界字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境也,从田,介声”,本义是田的边界。古时的世界,就是“三十年”加上“有限的面积”,是很小的。后来逐渐变大到包括一切,这正是一个引导着人们不断去冲破的过程。人的一生何尝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只能经历有限的一点时间、占据有限的一点空间,然而从幼年到壮年,从稚嫩到成熟,就是一个从最初的狭窄不断开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有界限的遗憾,但更多的是“我来过”的自信。所以清朝赵翼的一首小诗才会让人如此感慨:“千人万人中,有我七尺身。千年万年中,有我数十春。”
说到世,最常用的义项是用来指代我们生活的尘世间,由此便有了入世、出世等说法。入世与出世,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普遍存在一种的精神矛盾,不知有多少人在“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与“田园将芜胡不归”之间徘徊、纠结。中国文化里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儒道两家,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儒家主张入世,是一种进取性的文化,称“致虚极,守静笃”的道家注重出世,是一种退守性的文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古典文学中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描绘纵于山水、安于田园、耽于劳动、乐于归隐的诗歌,其作者反倒是远离山水、深居庙堂、身居高位、久在仕途。他们用笔耕不辍的诗篇,详尽地描绘着自己的隐士形象,描摹着一幅幅绿水青山、渔歌桨橹的画卷;尽情地用墨色的诗文画笔,涂写出色彩的灿烂斑斓;用有限的五言七言,勾勒出无限的大千世界。
其实,无论山水诗还是田园诗,无论是作画、弹琴、读书还是品茶、赏花、雅聚,这些都是中国文人们寻找到的用以平衡入世的责任担当与出世的情怀追求的方法,是他们精神放松、驰骋、安顿、调节的方式:文人正因为入世太深,才渴求出世;正认为身在城市,才艳羡山水;正因为人有心、话有意,才衬托出云无心、水自在……然而最可贵的是,无论山水还是田园,都只是他们人生起伏和心灵收放的经停一站,是他们求索阵地旁一个小憩的后院,很少会真是他们的终点。他们大多在休憩和调养了心灵的伤口之后,继续上路,继续关注社会、投入自己。因为他们太深地背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责任,太久地追寻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逃避尘世、放任自己、安逸度日、不问世事,往往是他们无法习惯更无法接受的辜负了自己一生教诲的行为--因为中国知识分子讲,即使穷途末路、即使世道艰难,也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寻找光明的出路。因此,纵使一时忘情山水,他们也不忘为守护更多山水田园之间的广大人民而作战在甚嚣尘上的世间前线。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曾说:“以出世的态度做人,以入世的态度做事。”一辈子也好,三十年也好,愿我们能如古人那般,有入世的担当和出世的情怀,能心在诗里闲庭信步,身在尘世安步当车,既欣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奋然进取,也向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淡然洒脱,这便是如此精彩的一世。
来源:微信公众号“zyjwjcbwz”